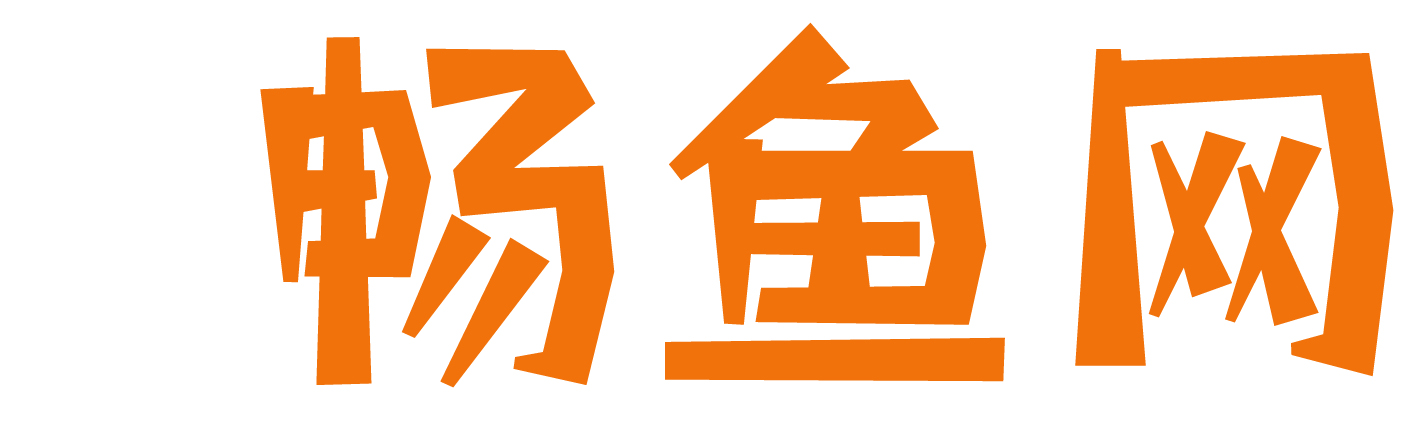一辰
一地洁白的棉花,能占领我的梦境,那还是多年以后的事情。然而,在故乡,我的梦境早已镌刻上洁白的棉花。
父亲小心翼翼地拿出棉花种子,小心谨慎地浸种发芽。直到时机成熟了,才发布植棉的命令。
一家人都戴上手套,跨着篮子,带上棉种,扛起锄头,奔赴田野。这是我家最大的一块土地,为了增加收入,每年都要种七八亩棉花。刨土的挖窑并保持合理间距,丢种子要封土且要不厚不薄。大家种完就算忙其他事情了了。可是,父亲种完了,才算开始。他不时地翻看那些种子,墒情如何,是否发芽,长势咋样,有无病虫,是否要浇水,诸如此类,父亲总要三思而后行。记忆犹新的是,每次吃饭时,母亲总叫我去地里喊父亲,而父亲一准是在棉花地里薅草、摘狂枝或逮虫子。起初,我也乐此不疲地去地里,可是喊了几遍总是无济于事,父亲总是边答应边继续忙;后来,我就有点抱怨,觉得父亲太过认真,纯属多余;长大了,我才知道,其实那些棉花也是父亲的孩子。如果说父亲从我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希望的话,他从那些洁白的棉花身上看到的则是另一种希望。
那时,商品经济已悄然兴起,街上做生意的个体户日渐活跃起来。母亲就唠叨父亲一根筋,死脑子,不会做点生意补贴家用。我隐隐约约地知道,父亲是队里的会计,管着一队的账呢。如果是队里有事情,父亲就派我挨家挨户去通知,所以我从小就兼着父亲的小秘书或通讯员。那时,我还跟着母亲附和,现在我才懂得父亲始终没动用队里钱的原因。因为父亲公私分得很清,他心里有杆秤,不能动就是不能动,谁说了也不行!
棉花苗长得出奇的齐整,这完全在父亲的掌控之中,只要不是种子故意与他作对,他完全可以让这些种子发挥出超常价值。
每天早上,父亲吆喝家人上地干活时,起得并不是很齐。很多时候,哥哥们也有埋怨,像我一样,也想睡个自然醒。周末或是节假日时,睡得再香,父亲也要把我揪起来去干活。我睁开朦胧的睡眼,用井拔凉洗了两次,还是睁不开眼。这时,父亲早已经一个人走了。我迷迷糊糊在跟在后面,觉得父亲对他的小儿子是那么严酷!事实上,我那时还小,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劳力,干不了多少活儿。然而,正是那时的劳动锻炼,让我提早对生活和未来有了深入的感悟。
父亲收拾过的棉田干干净净,像是用扫帚清理过一般,村里的人从那里经过都要赞叹一番。那些棉花苗积蓄着力量,在田野里快速地生长。每年锄过两遍地,就轮到逮虫子、喷洒农药和摘棉花了。
棉花的主干不断长高,直到高出我的头顶。清晨,我们人手一个瓶子,钻进茂密的棉花地,与那些白白胖胖的虫子作斗争。它们无恶不作,在叶子上、花朵上、棉桃上,所到之处,都会被啃噬得斑驳陆离。经过一夜休息,它们都出来了,像是一个个罪大恶极的侵略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到处搞破坏。我们眼疾手快,看准一个,抓住就装进瓶子里。那些被逮的虫子,踩着同伴的身体,在瓶子里爬来爬去,也未能走出去,最终让贪吃的家禽美餐一顿。
喷洒农药也是一个体力活。通常午后或是傍晚,整个田野里都有很多人在劳作。我们带上打药桶、农药、水桶和塑料盆,准备到棉田打药。由于家里种的棉花多,通常得用两个打药桶一起打,才能在天黑前打完。我帮父亲担担水,倒倒水,或是帮父亲把药桶递到肩上。不仅是打药,还要懂得农药配比:药少了不顶事,虫子打不死;药多了,又太浪费。打药的时候,我就在地头等。水少了,我就去水沟里挑水,直到药打完了,再帮忙换一桶。这个季节,田野里热得让人汗流浃背。不过,幸运的是,我家地头长着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它们带给我足够的阴凉。有时,我也带着书,见缝插针阅读一会儿。我有时闻着那刺鼻的农药味儿,感觉像中毒了一般。父亲站在棉花地里,背着一个装满药水的绿色打药桶,在一步步向前。他的左手握着拉杆,有规律地用力抽着药水,右手擎着一个长长的喷雾器,不时地在棉花的左右、上下、前后喷洒着。我看到父亲的渺小,他在棉花地里,只露出一个头,尤其是走远了,我甚至看不到他的身影,他完全消失在棉花田里了。打药隔三差五,若是发现了新的虫子,或是棉花生了其他病,或是缺了哪些营养,更要增加频次或换药。
棉花次第开放的时候,是一种美丽的奇观。整个田野里,像是立刻生出了不计其数的白色蝴蝶,高高低低地伫立在棉花的枝头;又像是千万朵白云,瞬间幻化出千姿百态。我们下午拉着架子车,再把车子的一圈用栅栏围起来,以装上更多的棉花。篮子,筐子,篓子,袋子,只要是便于拿的,均被我们排上了用场。我们一边走一边连着花的外壳儿一起采摘,中间几乎不能休息,这样才能在天黑前将棉花摘完。若是赶上人手不够或是去地里晚了,非要到傍晚以后趁着月亮摘完,因为第二天又要摘新的棉花。
棉花盛开的时候,白天可要摘几车。晚饭后,依然不能睡觉,还要在院子里将花壳摘去,才能第二天接续上新花。那时,奶奶还健在,一到晚上,就和我们一起摘花。摘花也有技巧,可不是简单地将花摘出来就行,还得把花上的碎叶子摘掉,不然,花不干净就卖不上好价钱。因为要摘很多,摘着摘着就打瞌睡了。奶奶看我坚持不住了,就让我先睡,可是等到了睡了一觉,我还看到院里的灯依然在亮着,不时地还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若是没有弄完,还要接着摘,一边摘一边晒,父亲还要把摘不净的棉花再清理一遍。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喜欢戴着个凉帽,在太阳下翻晒整理棉花的样子,那种对待一丝不苟的态度,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晾晒的地点有时在院子里,有时在临公路的边缘,总之都要有充足的阳光照射,才能将棉花晒得又柔又干又白。
一袋袋的棉花晒好了,堆满了屋子,父亲很是开心。那时,商品经济还不发达,棉花也是国家统购统销,所以要到棉花库。我们拉着棉花去售卖,要排很长的一队。卖过棉花,不仅换了不少钱,还可兑换一些棉花油。现在虽然不再有人使用,那时却是一种食用油。母亲常用这些棉油变着法儿给我们做好吃的。
我时常从一个带着棉花的梦境进入另一个带着棉花的梦境,在那些梦境里,母亲用洁白的棉花为我们做了许多与温暖有关的东西——棉被、棉帽、棉袄、棉裤、棉手套、棉鞋……冬天里,被烧得通红的木头在火盆里散发着温度,我们围坐在火盆的周围,烤着手,烤着脚,我们说着,笑着,想着……
2022.5.23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E-MAIL:dandanxi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