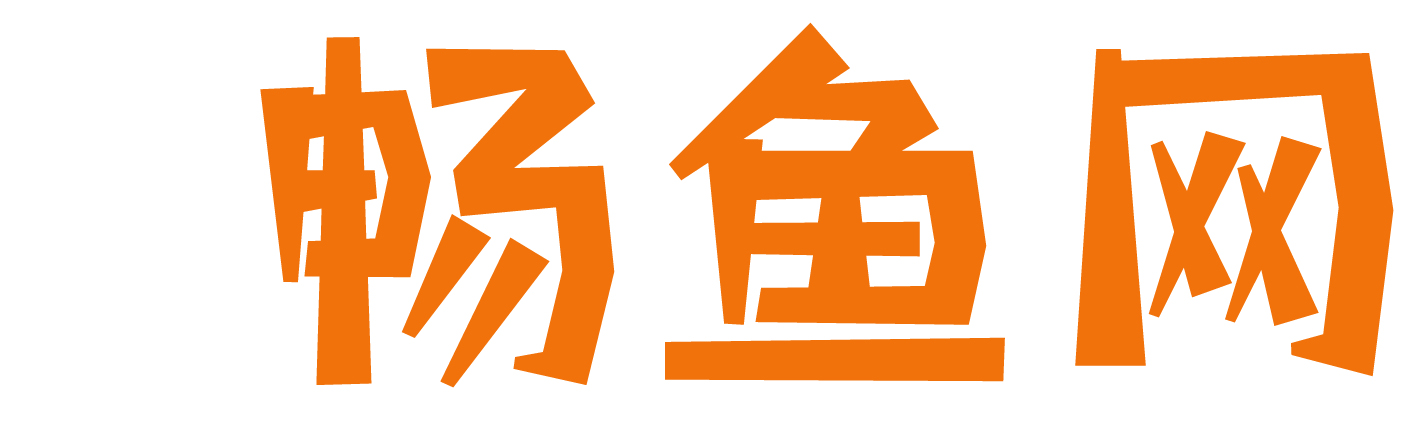很多的阳光,像大雨一样,铺天盖地。它们毫不吝啬地闯进这个不大的小院里,我怀疑它睡懵了,走错了地方。
我走在灰白色的石砖上,这些石砖整齐地排列着,在小院里延伸,直到屋墙和篱笆。它们之间的缝隙里,几根野草在雨水肆虐之后,顽强地拱出来;还有不知名的野菜,也羞涩地亮出几片嫩叶。偏僻的墙角,有一株蒲公英,银白的伞球静候着风把它吹向天涯。
夏天已经很深了,我以前来到这里,满园的绿色围绕着我,这石砖上斑驳的影子,像一些调皮的精灵,在阳光下跳呀跳呀,我不去理它们,只任植物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屋檐下有一棵大椿树,它从时间里从容走过,高过倾斜着的红瓦的屋檐和屋脊。后来它衰败了,零乱的枝叶,稀稀疏疏,孤独而茫然。
这棵树后来消失了,在房子往前扩展了一米玻璃罩墙之后。生命被铲除,被遗忘,春天依然来临,植物依然葱绿。慢慢地,它淡出了我的记忆,一片碧绿簇拥着红艳的美人蕉代替了它们曾经的影像。还有那一丛绿竹,邻居家的竹子蔓延过来,在窗前长成一簇簇细密的竹丛,在深夜的风里,“刷拉拉”响个不停。如今,那些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它们纤细的叶子以及小院的主人,又在哪里呢?
呼吸着树叶子吐出的微凉的气息,仿佛听到一声声轻轻的呼唤,“哗啦啦”,仔细辨别又好像是叶子与风的和鸣。我模糊地看到一个人影,是在梦境里熟悉的,她在石砖上迈着轻盈的步子,微笑着,向我走过来。
每年夏天,我与它有一个约会。静谧的院落,里里外外都是树。墙外的大核桃树遮天蔽日,硕果满满;枣树收敛着枝叶,蓬蓬勃勃抱成一团,一串串青果与叶子的形状大小差不多,只是果实泛着油油的白。院内的柿子树,挺拔高耸,如世外高人,只是在雨天,“砰”地一声轰响,一颗硕大的果实穿过稠密的叶子,冷不丁砸下来,它只是忍着,默不作声。无花果树像一位老人,伸开胳膊,张开大手迎接着你,每天递给你甜蜜蜜的果实。
房子和院子的历史太久远了,当初是高大崭新的红砖瓦房,比周围的建筑气派得多。如今它蜷缩在高楼大厦的缝隙里,贫弱如一乞儿。
我闭了眼,在黑暗的隧道里旋转下沉,跌落在最初的时刻。我是一个少年,身轻如燕,院门永远向我打开着,热乎乎的饭菜,暖暖的被窝,还有早晨睡意朦胧里,母亲一声声呼唤我乳名。
我走路是脚下生风的,院里的菜畦一般不会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瓜叶破土,整齐地画一道绿线,慢慢变粗,变立体,最后成为一架,密密麻麻侵占院子里的空间。饭桌上的餐盘里的菜蔬新鲜可口,我狼吞虎咽之后,依然不愿在小院里过多停留。那个年龄的我,外面的诱惑实在太大。
我站在院子里,站在砖石的地面上,那时,砖石的缝隙里褐色的土里没有一根野草。那些草长在我的脑袋里,疯狂地生长,小小的院落根本承载不了它们。那一天,我背起母亲缝制的帆布包,圆滚滚的,塞满衣物及日常用品。我大踏步走出院子,没有一点留恋。长硬了翅膀的小鸟,要试一试自己能飞多远。乘上去远方的长途汽车,经过陌生的田野和河流,在新的人群里,知识的海洋里,放飞青春。渐渐的,我仿佛飘起来,春天暖烘烘的气息要将我融化,在异地的天空,我是一只风筝,无拘无束的飞啊,飞啊,终于有一天我好像是掉了什么,怅然若失,良久,我突然意识到,一直牵着我的线断了,我长期依赖的那根绳的力量不在了,恐惧之后,淡淡的惆怅纠缠着我。第一次尝到思乡的滋味,也深深地体味到何谓归心似箭。
我又站在小院里了。放假的那一天漆黑的凌晨,我背着行囊,如一个夜行的盗贼,一个人徒步走过灯火阑珊的街道,偶尔有清洁工大声的交谈,扫帚摩擦水泥地面的唰啦唰啦声,在我耳边轰响。我疾步如飞。穿过一条条街道,坐上最早的一班车,直奔家的方向。“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大半天的征程之后,我闯进小院的大门,心扑扑地跳着,喘着气,朝着蹲在地上翻晒东西的母亲,大声喊一声:“娘!”
母亲惊喜的目光,熄灭了熊熊燃烧的思乡之火,我如灰烬一般安静地坐在屋前的石阶上,享受着小院里明媚的秋光。时空仿佛定格在那里,青春的烦恼,纷乱如麻,我一次次挥刀要斩断它们的时候,不小心伤了自己的心。忧伤密布在空气里,泪水时时浸润着。母亲不多说话,我沉默着,任时光洗刷沉淀在青春岁月里的阴郁。那一刻,我就是一枚秋风里叶子,飘摇,坚挺着,倔强地对抗着肆虐的冷风。
我时常在院子里徘徊,静谧的时光,看夕阳穿过稀疏的树叶洒下来,墙上斑驳的影子晃动着。我的心也随之摇动,无声息地吐纳祥和的空气。我不想离开那里,它是属于我的宫殿,虽然不是富丽堂皇,却是心灵安歇的港湾。我的情绪影响着它,它的缄默给我无形的压力。
无数个日夜之后,我穿上鲜红的嫁衣,在母亲满脸的泪痕里,迈开沉重的步子,登上婚车的那一刻,我知道它一定在我转身离去之后,掩面哭泣,没有谁看得见。
走出去多远,回头,它就在那里。在一片瓦房之间,在那条熟悉的街道上。我时常隐隐地觉得它一次次的召唤,在幽深的梦里,黑暗的走不到头的道路,所指的总是它的方向。我孤独的灵魂,千百次地摸索着前行,旷野里的大风吹着,冰天雪地里匍匐着,它是一个模糊的坐标,窈窕,刻骨,夜夜缠绕着,挥之不去。它让我的生命的知觉进一步拓展,在另一个时空里,给我更多的暗示和隐喻。
我站在西屋的门口,看烧水的煤气灶“哧哧”冒着蓝色的火苗,门外窗下空阔的一片。那年回家过年,腊月二十八,家家厨房里都忙着炸东西。我系着围裙,把金黄的藕夹捞出来,滚热的油锅上,笊篱滴着油。我努力伸长胳膊,怕油溅在身上。母亲在窗前站着,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低地,对我说:“你小姨死了,她得了抑郁症,上吊了。”一块大石头砸晕了我,头木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突然觉得那个冬天真冷,寒气透过厚实的羽绒服直逼着脊梁骨。我不知道怎么能安慰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在几百里外的老家,母亲唯一的亲人——小姨,在家人的厌弃里,自绝于世了。我呆愣愣地机械地操作着,心,一直向下沉。
两年后的今天,我还是站在这里,眼前空荡荡的,不时有黑蚊子袭击裸露的皮肤。窗下,一塑料垃圾桶,用电线穿过做提芯,里面装着炭灰,沉甸甸的。母亲身体瘦弱,提着它,一定感觉很重,可是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用这只桶把炭灰送到一百多米外的垃圾池里去。
我站在此刻的小院里,陷在记忆里,恍惚不知是在昨日还是今朝。幸福和痛苦,像隔着一条河流——母亲的离世,那一条我不愿触碰的洪流,黑色浪涛卷走最初的安宁和最纯真的美好,也流去我无数个日日夜夜汹涌而来的泪水。女儿在一张纸上写着:“经历了姥姥去世,再读余华的《活着》,才懂得福贵失去亲人,那些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话后面,是怎样的肝肠寸断。”
小院里屋子越来越陈旧了,落雨天屋脊会渗水。前几年,母亲还亲自爬上屋顶,重新整理那些疏散了的瓦片。有几次听说小院要拆迁,又因为种种原因搁浅了。我是希望它永远在那里,留着我的记忆,等在岁月的长河里。
我一步步踱着,丈量着时光的长度,沿着神秘的隧道,不停地走下去。一道硕大的石门“砰”的一声,在我身后关闭。我被时间无情地驱逐,遗弃在这个残缺的世界上。我清楚地知道,即使我还在这个小院里,也永远回不到从前了。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吕延梅,笔名,绿叶子66,七十年代出生,生活在孔孟之乡,高级语文教师。工作之余,唯喜读书写字,多年来一直坚持散文创作。作品曾经发表于《当代小说》《中国工人》《现代语文》《新潮》《济宁日报》等杂志报刊。一些文章已被多家网站收录转载。

东方散文,感情求真,思想求深,角度求新,视野求广,语言求美。请支持如下稿件:人性之美、大爱情怀、乡愁、亲情友情爱情、生态情怀、性灵自然等。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E-MAIL:dandanxi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