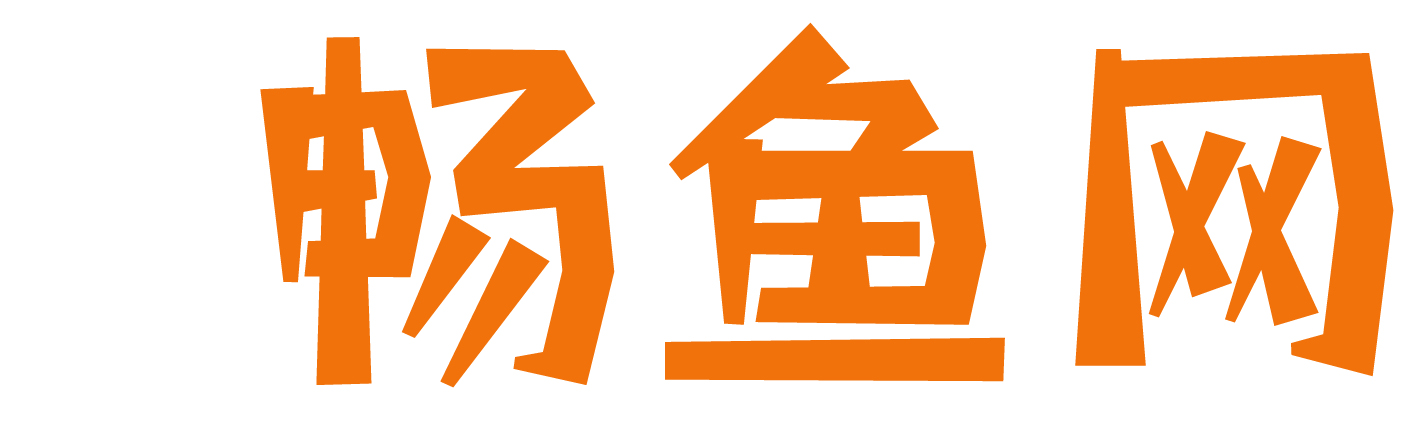仲夏之初,值天大热。偶读东坡《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稍有感焉。觉此老遇事达观,造语清寥,千载而下,犹获我心。实宜泛览其书,权作修身养性之用。

东坡扶杖醉坐图(上海博物馆藏)
月中因审稿所及,需覆覈文本。检东坡题跋、《志林》,偶有疑于前人断句处,觅其旧椠,以参新刊,两相雠校,亦未解其惑。爰事考订,详寻其源,旁及左右,竟是疑窦丛生。遂穷数月力,作一番辨析。钩沉探赜,无非小题大做;索隐发微,只求来踪去迹。今于题跋、《志林》,各得其一焉。
一、苏东坡的宝镜
赵宋开国,务农兴学,制礼作乐,自以“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崇古之风遂起,古器收藏与研究亦渐成时尚。蔡絛《铁围山丛谈》载: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后世。……国朝来寖乃珍重,始则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则若伯父君谟、东坡数公。……学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风遂一煽矣。元丰后,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
及宋徽宗广事搜罗,作《宣和博古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致“天下冢墓,破伐殆尽”。东坡师友若欧阳修(永叔)、蔡襄(君谟)、文同(与可)、刘敞(原父)、李公麟(伯时)辈,皆通鼎彝之学,东坡稍有参与其间,故入“从而和之”者之列。

《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出版)
今观东坡集与同时人诗文,多有相关记述者,东坡唯不致力于收罗耳。其涉及古器物之诗文,诗有《胡穆秀才遗古铜器似鼎而小上有两柱可以覆而不蹶以为鼎则不足疑其饮器也胡有诗答之》、《次韵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间刘购得之》、《凤翔八观》数首,题跋则有《书陆道士镜砚》、《书所获镜铭》、《书黄州古编钟》、《书古铜鼎》、《书金錞形制》诸篇。其中《书陆道士镜砚》、《书所获镜铭》二篇颇可注意。
陆道士名惟忠,字子厚,眉州眉山人。与东坡有交游,故东坡题其镜,兼及己之所藏,并作考释。按,东坡于宋神宗元丰四年(辛酉,1081)正月路过黄州故城,获得汉镜一枚。此镜东坡集内数次提及,后世各本俱有著录,今与他书所记,互为对读,颇有可辨处。

茅维编《东坡先生全集》卷七十(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茅维编《东坡先生全集》卷七十题跋《书陆道士镜砚》曰:
陆道士蓄一镜一研,皆可宝。研圆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却月金文;甚能克墨而宜笔,盖唐以前物也。镜则古矣,其背文不可识。
家有镜,正类是。其铭曰:“汉有善铜出白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俌之。”
以铭文考之,则此镜乃汉物也耶?
吾尝以示苏子容。子容以博学名世,曰:“此镜以前皆作此,盖禹鼎象物之遗法也。白阳,今无此地名。楚有白公,取南阳白水为邑,白阳岂白水乎?汉人‘而’、‘如’通用。”皆子容云。
镜心微凸,镜面小而直,学道者谓是聚神镜也。
丙子十二月初一日书。
按,苏子容(1020—1101)名颂,原籍泉州同安,徙居润州丹阳,遂以丹阳为籍。宋神宗熙宁初,曾与东坡同朝共事;后多往还,亦多诗文唱和。
卷六十六题跋《书所获镜铭》曰:
元丰四年正月,余自齐安往岐亭,泛舟而还。
过古黄州,获一镜,周尺有二寸,其背铭云:“汉有善铜出白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俌之。”
其字如菽大,杂篆隶,甚精妙。
白阳,疑南阳白水之阳也。
其铜黑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照人微小。旧闻古镜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茅维编《东坡先生全集》卷六十六(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又卷五十三尺牍《答李方叔十七首》第二首有曰:
近获一铜镜,如漆色,光明冷彻。
背有铭云:“汉有善铜出白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俌之。”
字体杂篆隶,真汉时字也。
白阳不知所在,岂南阳白水阳乎?“如”字应作“而”字使耳。“左龙右虎”,皆未甚晓。
更闲,为考之。

茅维编《东坡先生全集》卷五十三(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按,李方叔(1059—1109)名廌,颍昌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为苏门六学士之一。尝贽文谒苏轼于黄州,苏轼谓其笔势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王直方《诗文发源》云:“李方叔为坡公客。公知贡举而方叔下第。”东坡有诗题曰:“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三篇所述,为同一器。
就三篇文字内容及先后言:
《答李方叔十七首》题下注“以下俱黄州”(元丰三年二月至元丰七年四月,东坡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黄州,今湖北黄冈),第二首云“近获一铜镜”,则作于获镜后不久,涉镜色、铭文、字体,并考铭文“白阳”、“如”、“左龙右虎”三处。且请李方叔得闲时,为更考“白阳”、“左龙右虎”之意。据《书陆道士镜砚》,“如”字作“而”字用,实系得诸苏子容所云,则苏子容知此事,必在东坡得镜后不久,且在致函李方叔之前。
《书所获镜铭》作于《答李方叔》后,记得镜之时为元丰四年(辛酉,1081)正月,得镜之地为古黄州(地近今湖北黄冈西南),涉镜色、镜形、铭文、字体,并考铭文“白阳”一处,且言古镜之功用(道家聚形之法)。赵希鹄《洞天清录》曰:“古铜器多能辟祟,人家宜畜之。”是其意也。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曰:“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书陆道士镜砚》“镜心微凸,镜面小而直”、《书所获镜铭》“其明照人微小”,所言与之俱合。
《书陆道士镜砚》作于宋哲宗绍圣三年(丙子,1096,时谪居惠州)十二月初一,去获镜已十有五年。涉镜形、铭文,并示古镜之功用(学道者谓是聚神镜)。至于铭文内“白阳”、“如”二处之说,谓皆是以博学名世之苏子容所与言之者。
三篇文字所录镜铭十九字,无异文。
汉代镜铭,概多韵语,以三四五七言为主。此镜铭十九字,“阳”、“明”为韵;“清、明”为语,即所谓“汉清明鉴”是也。此类铜镜后世出土者亦多,揆诸宋以降著录之铜镜铭文,文字仿佛者,如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七引《博古图》有铭曰:
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顺阴阳。

周世荣《湖南出土汉代铜镜文字研究》附图
又如汉代广陵国铜器有“汉有善铜”神兽博局镜,其铭曰:
汉有善铜出丹阳,取之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備四旁,朱爵玄武顺阴阳。
湖南长沙亦曾出土一枚铜镜,铭曰:
汉有善铜出丹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備之。
此铭文与东坡所藏者,除“丹”、“備”二字外,馀无二致。

黄濬《尊古斋古镜集景》
据《中国铜镜图典》、《汉镜铭文汇释》诸书著录,镜铭韵文之全或不全,字之正讹与否,颇为随意。“取为镜,清而明”之用,《汉镜铭文汇释》著录一枚,铭曰:“汉善同,出丹阳。取之为竟,青而明。左龙右虎主。”清初倪涛《六艺之一录》卷十八“汉清明鉴二”亦有十四字图铭:“汉有善锡出白阳,取之为镜清且明。”可见一斑。

《侯鲭录》卷一(明正德间鳌峰书院刻本)
与东坡有关之铜镜故事,他处亦多有记录。其好友赵令畤《侯鲭录》卷一载录一条:
余家有古镜,背铭云:“汉有善铜出丹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補之。”不知“丹阳”何语,问东坡,亦不解。后见《神仙药名隐诀》云:“铜,一名丹阳。”……东坡云:“‘清如明’,如,而也,若《左传》‘星陨如雨’。”
倪涛《六艺之一录》卷十八亦记曰:
黄山谷曰:余家有古镜,背铭云:“汉有善铜出丹阳,取为镜,清且明,左龙右虎補之。”不知“丹阳”何语,问东坡,亦不解。后见《神仙隐诀》云:“铜,一名丹阳。”……东坡云:“‘清如明’,如,而也,若《左传》‘星陨如雨’。”
观此二条所记,一曰赵令畤“家有古镜”,一曰黄山谷“家有古镜”,与东坡自记如出一辙,颇有可疑处。
综上所记,有数事需作梳理:

二,镜铭“清如明”之“如”字,作“而”解,《春秋》“星陨如雨”,杜预注:“如,而也。”欧阳修《后汉郭先生碑》(集本):“其曰‘宽舒如好施’,盖以‘如’字为‘而’也。《春秋》书‘星陨如雨’,释者曰:‘如,而也。’然施于文章,以‘如’为‘而’,始见于此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如字训而”条:“欧阳公《集古录》载《后汉郭先生碑》云:‘其长也,宽舒如好施,是以宗族归怀。’东坡得古镜,背有铭云:‘汉有善铜出白杨,取为镜,清如明。’皆训‘如’为‘而’也。”并谓《后汉郭先生碑》碑文、古铜镜铭文训“如”为“而”,分别出自欧阳修、苏东坡之解释。然东坡自谓“‘而’、‘如’通用”,实是苏子容告之者也。
三,赵令畤、黄山谷“家有古镜”事颇可疑。苏东坡曰“家有镜”,出于自记,且数见于集中,赵、黄二镜铭云:“汉有善铜出丹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補之。”与东坡藏镜铭仅“白”作“丹”、“俌”作“補”之别。赵令畤虽与东坡同时,然《侯鲭录》之编定,据孔凡礼先生考证,“本书刊刻时,赵令畤是否在世,已不可考”;孔先生用作底本之清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侯鲭录》,鲍氏于某些条目“是否以己意增之而偶失说明?亦不可得其详”云。此条或为后人伪托。或者东坡后将该镜赠与赵令畤,且告以不知“白阳”为何意,故有此记,亦未可知。然若此时已释作“丹阳”,与“善铜”连属,熟诵《汉书》如东坡者(参见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一“东坡钞汉书”条),岂有不知之理!倪涛《六艺之一录》全书四百馀卷,成稿于清乾隆时期,原即为书学文献纂集类著作。其钞录资料,一般皆注明来源,如《太平广记》例。然所谓“黄山谷曰”云者条,稿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末俱脱出处,且其文与赵令畤《侯鲭录》几乎完全一致,倪氏“赵”冠而“黄”戴者,传钞之误欤!抑有意为之欤?实不可知也已。
二、李邦直的自嘲
宋人作字,盖皆自存其稿,备将来编文集之用。观东坡诗文集之裒然巨帙,井然有序,是可知矣。今唯《东坡志林》,稍觉芜杂,其文字与入诗文集者,亦多有仿佛处。
宋哲宗元符三年(庚辰,1100)东坡自海南北归时,与郑靖老札有“《志林》竟未成”句,则《志林》当是东坡自定拟撰之书也。惜未成。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曰:“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曰:“《东坡手泽》三卷,苏轼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者也。”《东坡手泽》不传,未审其与今本《志林》之关系。
今传之《东坡志林》,刻本有宋左圭《百川学海》一卷本、明万历赵开美校刊五卷本、明万历焦竑评点五卷本、明万历商濬编刻《稗海》之十二卷本。一卷本仅史论十三篇,或即东坡撰《志林》之旨欤?后人据东坡遗稿、杂钞等手泽,汇编而成《东坡志林》若干卷,且在流传过程中,或有好事者阑入其他文字,致使体例错乱,条目芜杂,真伪莫辨。

《东坡志林》目录(明万历二十三年赵开美校刊本)
兹以《李邦直言周瑜》一条,稍作演绎。
赵开美校刊五卷本于每一条皆拟一小标题,卷首并置“目录”。《李邦直言周瑜》条居卷四,前一条为《王嘉轻减法律事见梁统传》,后一条为《刘聪吴中高士二事》。其所对应之正文:
王嘉轻减法律事见梁统传
汉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习所见以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罢肉刑与参夷之诛景帝复孥戮晁错武帝罪戾有增无损宣帝治尚严因武之旧至王嘉为相始轻减法律遂至东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记其事事见梁统传固可谓疏略矣嘉贤相也轻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记乎统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兴哀平以轻法衰因上书乞增重法律赖当时不从其议此如人年少时不节酒色而安老后虽节而病见此便谓酒可以延年可乎统亦东京名臣一出此言遂获罪于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灭族呜呼悲夫戒哉疏而不漏可不惧乎
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经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饭贤愚相远如叔安上言吾子以快活未知孰贤与否
勃逊之
勃逊之会议于颍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逊之曰菊当以黄为正馀可鄙也昔叔向闻鬷蔑一言得其为人予于逊之亦云然
刘聪吴中高士二事
刘聪闻当为须遮国王则不复惧死人之爱富贵有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吴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于生者

《东坡志林》卷四(明万历二十三年赵开美校刊本)
标题前空两字,正文皆顶格。正文《勃逊之》一条,目录未出。
商濬编刻十二卷本无“目录”,正文每一条亦无拟题。《李邦直言周瑜》条居卷二,其正文(含前后条):
韩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文畅之意尔非信佛法也
世乃妄撰退之与大颠书其词凡陋退之家奴仆
亦无此语有一士人又于其末妄题云欧阳永叔
谓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诬永叔也永叔作醉
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尔又不自以为奇特也
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
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又不能为吾醉翁亭
记此又大妄也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乙帐耳
了无可观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经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
善饭贤愚相远如此安上言吾子似快活未知孰贤与否【说明:“未知孰贤与否”六字,小字双行,版式参见下图】
与朱 勃逊之会议于颍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
新枝而菊品尤多逊之曰菊当以黄为主馀可鄙
也昔叔向闻鬷蔑一言得其为人予于逊之亦云
然
汉武帝违韩安国而用王恢然卒杀恢是有秦穆违
蹇叔之罪而无用孟明之德也

《东坡志林》卷二(明万历商氏半野堂刻《稗海》后印本)
正文每条第一行顶格,回行退一字。《李邦直言周瑜》条末,“未知孰贤与否”六字作双行夹注,占三字,适满行;“与朱”条,“与朱”与“勃逊之”间空缺两字。对比以上二本,赵刊五卷本正文溢出《勃逊之》一条,有文无目;商刻十二卷本正文“与朱 勃逊之”云云则独立为一条。中华书局整理本以赵开美五卷本为底本,点校者王松龄先生于“未知孰贤与否”处出校记曰:
《稗海》本卷二此条与下条误合为一,作“未知孰贤与朱勃逊之会议于颍”,是则此句当作“未知孰贤”。“与”字属下条,无“否”字。
今所见《稗海》诸万历印本,“未知孰贤与否”六字俱为双行小字,由此推测:点校者所见者必为初刻初印本(或试印本),其字号与前后一致,且单行,即:“未知孰”次“快活”之下,“贤与否”置“勃逊之”之上(此行行首退一字),作为一篇之内容,行内字数适相衔接也。然意思实不相干,后经校阅者指出,故《稗海》后印本即挖版改作两条矣。

《东坡志林》卷二(明万历商濬编刻《稗海》初刻初印本)
曾就此事联系王松龄先生,得示曰:“我所用《稗海》本当为上海师院图书馆所藏明清刻本。”即请李玉栓兄代为翻检,发来书影,其文字版式,果如予所测焉。是知商氏所据之原本,实为一条也必矣。
赵开美校刊本卷首有其父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于此书之梓刻曰:
余友汤君云孙,博学好古,其文词甚类长公。尝手录是编,刻未竟而会病卒。余子开美因拾其遗,复梓而卒其业,且为校定讹谬,得数百言。庶几汤君之志不孤,而坡翁之在当时其趑趄于世途、鞿缚于穷愁者,亦略可见云。
由是可知,五卷本《志林》,实为赵用贤友人汤云孙手录并付刻者,刻未竟而汤氏病逝,后经赵用贤之子赵开美为校订讹误,遂得续刻而成。

茅维编《东坡先生全集》卷六十六(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汤氏五卷所据何本?未有交代。商氏十二卷何所从来?不得而知。且茅维编《东坡先生全集》卷六十六与毛九苞编《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三十七,皆同时前后收入《记王彭论曹刘之泽》、《记李邦直言周瑜》二条(一为王彭论曹操、刘备,一为李邦直论周瑜,所论皆三国人物),——则四人当各有所本。今人已考赵开美校刊本卷二《记刘梦得有诗记罗浮山》文字拼接自东坡《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之自注,卷三《梁上君子》、《太白山旧封公爵》诸条,亦系后人伪造,(参章培恒、徐艳《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兼谈十二卷本〈东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文;然元刘壎(1240—1319)《隐居通议》卷二十五《小儿听古话》条,谓“《东坡别集·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子薄劣”云,即诸本之《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条也,此条当不伪。是元人所见之《志林》,或为《东坡别集》内之一种欤?识此待考。)并指出《勃逊之》条出自《赠朱逊之》诗小引。

刘壎《隐居通议》卷二十五(清康熙间钞本)
以此反观《李邦直言周瑜》、《勃逊之》二条,两本虽皆前后连属,然五卷本之目录与正文不一,十二卷本版刻小字与空缺并存,其所据原本皆误作一条也必矣。兹为校理二条文字如次: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经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饭,贤愚相远如此。”安上言:“吾子似快活,未知孰贤?”
与朱勃逊之会议于颍。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逊之曰:“菊当以黄为正,馀可鄙也。”昔叔向闻鬷蔑一言,得其为人,予于逊之亦云然。
按,“未知孰贤”下“与否”二字,实为后一条“与朱”之讹。盖因“与朱”讹作“与否”,且连上读,致“未知孰贤与否”六字不句,并复使“勃逊之”三字不词。

《东坡先生志林》卷二(明钞本,国家图书馆藏)
《与朱勃逊之》条,即东坡《赠朱逊之》诗之小引:“元祐六年九月,与朱逊之会议于颍”云云。朱勃,字逊之,元祐元年(庚午,1090)五月为承议郎,六年九月任京西运判。东坡与“会议”者,为陈州开八丈沟事,可参东坡《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二首》、《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诸文。


《东坡志林》卷四(明万历焦告评点本)
李邦直(1032—1102)名清臣,魏(今河北大名)人。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1053)进士,调邢州司户参军、和川令。嘉祐六年(辛丑,1061)与苏轼、苏辙、孙洙等同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未予秘阁试论。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1065)试秘阁为第一,授秘书郎,签书苏州节度判官。次年丁母忧,家居。宋神宗熙宁二年(己酉,1069)服除。正是这一年,王安石变法开启,李清臣成为变法之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熙宁三年(庚戌)夏四月〕癸未,虞部员外郎苏棁、秘书丞陈睦并为秘阁校理,秘书郎李清臣为集贤校理,江宁府推官刘挚为馆阁校勘,大理寺丞乐咸为太子中舍。(卷二百十,第5108页)
〔熙宁三年九月〕壬子,陕西宣抚判官、度支员外郎、直舍人院吕大防兼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曾布,宣抚司书写机密文字、秘书郎、集贤校理李清臣,大理寺丞李承之并充检正公事,布户房,清臣吏房,承之刑房,清臣、承之仍并改太子中允。(卷二百十五,第5245页)
〔熙宁三年十一月〕壬辰,上批:“陕西宣抚判官吕大防、管勾机宜文字李清臣,近除中书检正官,其敕告入递给付,以示选任之意。”从韩绛所请也。(卷二百十七,第5272页)
按,中书检正官于熙宁三年九月一日为变法所设,其职权主要有编修、详定诏敕条例,检举、督促诸司职事,提举在京百司事务,察访、处置地方事务,尤其是新法之执行情况,实为政务最为繁忙之机构是也。
李清臣自谓“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饭”,四十则熙宁四年(辛亥,1071)时,其果“多睡善饭”、无所事事者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二曰:
〔熙宁四年夏四月〕丙子,中书奏:检正中书吏房公事李清臣兼编修中书条例。诏罢之。寻自太子中允复为校书郎,通判海州。韩绛既责,清臣愿还旧秩,且求外任故也。(第5410页)
揆诸《长编》所记,可知熙宁三年九月,韩绛(1012—1088)宣抚陕西,奏请李清臣为宣抚使司书写机宜文字。由于韩绛“素不习兵事”,“复以种谔为鄜延钤辖”,致使“蕃兵皆怨望”。四年三月,西夏攻陷抚宁诸城,种谔“茫然失措,欲作书召燕达,战悸不能下笔”。宋神宗不得已,“诏弃啰兀城,治谔罪,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绛坐兴师败衄,罢知邓州”。李清臣因之受牵连,“规自全,多毁绛”,自求外任,神宗允而“薄之”。
晁补之《资政殿大学士李公行状》曰:
绛之贬也,公尚以中允为检正官。公曰:“我岂负韩公者!”因求还所迁秩,补外;复以秘书郎通判海州。会直舍人院孙洙出守海州,与洙同制科馆职,一时觞咏传淮海,为盛事。宽役法,免漕渠夫,去而民思之。
按,熙宁四年五月丙午,“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同知谏院、直舍人院孙洙知海州,从其请也”。是知孙洙、李清臣差不多同时出任海州职务。

《三苏年谱》(孔凡礼撰,中华书局出版)
据《宋史·孙洙传》,孙洙在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敛缗钱,以取赢为功,洙力争之。方春旱,发运使调民濬漕渠以通盐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其与李清臣“宽役法,免漕渠夫”二事,盖合力而为政者也。
至熙宁六年(癸丑,1073)六月丁丑,王安石与宋神宗论及张吉甫事,神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吉甫虽小人,陈义甚高,贤于李清臣远矣。”此时李清臣犹在海州。至于“公三为执政,遍践三省,勋封爵至上柱国、开国公,食邑实封所共加至六千九百户”云者,此乃后话。
故曰:李清臣自三十九岁至四十二三岁之间,历任(或有同时兼任)秘书郎、集贤校理、宣抚使司书写机宜文字、检正中书吏房公事、太子中允、校书郎、海州通判,公务繁忙,决不能自称为“多睡善饭”者也。
然则自嘲“多睡善饭”者,何人耶?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十(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检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十有《上张丞相书》一篇,曰:
某顷自宜春违远钧席,言归庐陵,杜门却扫,读书养亲者,又一年矣。
居恒自咎,以为周瑜二十四经略中原,相国春秋才四十,出入将相,身为天下重轻者十年于兹矣。仆年三十有五,徒多睡善饭,年来鬓发星星,览镜茫然。进不能出力补报明君,退不能取寸禄斗食以荣其亲,仅同幽蠹,日夜守蚩尤之庐,又不能效四体无骨者扫门拜尘于王公大人之前。往往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其胸中耿耿者固在。
近者侧闻相国奋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四海之士,皆愿身櫜键备奔走。仆固门下士也,穷愁无聊,不获挟粮以趋。然士为知己者死,辄敢不避斧钺之诛,冒进狂瞽之说,伏惟怜其志而少加察焉。
按,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张丞相即张浚(1097—1164)字德远,号紫岩,汉州绵竹(今四川)人。宋徽宗政和八年(戊戌,1118年)进士,南宋初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力主抗金,志在恢复。两人相差五岁。
胡铨于宋高宗建炎二年(戊申,1128)二十七岁时,以第五名进士及第,授左文林郎、抚州军事判官。张浚时任礼部侍郎,胡铨《祭张魏公文》曰:“建炎戊申,驻跸维扬。公为春官,贰卿文昌。详定殿庐,多士在庭。得铨大对,谓如刘蕡。”又欧阳守道《题家状序》:“张魏公第其文为进士第一,既而置之第五,虽第五,然有魏公之定论在,犹第一也。”故胡铨自称“门下士”。后以抵御金兵有功,转承直郎,权吉州军事判官。四年(庚戌,1130)秋,丁父忧,乡居庐陵;绍兴三年(癸丑,1133)三十二岁,服除,“无仕进意”(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或勉之仕,不答”(杨万里《胡公行状》)。

《周益文忠公集》卷三十(南宋刻本)
杨万里《宋故资政殿学士朝议大夫致仕庐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胡公行状》曰:
绍兴五年,忠献魏国张公浚都督诸路兵,辟公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司干办公事,改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召赴都堂审察。
周必大《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神道碑》曰:
绍兴五年,张忠献公都督诸路军马,辟湖北常平茶盐司干办公事,亲嫌,易湖南提点刑狱司,俱未行。召赴堂审察。
据《行状》与《神道碑》,可知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张浚为推举之两职务,胡铨俱未往任,时胡铨三十四岁矣。然则“召赴都堂审察”何时耶?
绍兴六年(丙辰,1136)正月,张浚视师荆襄,后进驻盱眙,并命韩世忠自承楚以图淮阳,刘光世进屯合肥,岳飞进驻襄阳,准备北伐中原。一时军民之心,为之大振。胡铨上张浚书“近者侧闻相国奋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四海之士,皆愿身櫜键备奔走”,盖即指此而言;并将之以周瑜“经略中原”作喻,亦颇为贴切。至是年十月,胡铨始“赴召都堂”(《妣焚黄文》),然犹未授予官职。
直到胡铨三十六岁,即绍兴七年(丁巳,1137)初,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荐,“夏四月,以上殿称旨,特改左通直郎”(《妣焚黄文》)。据胡铨《萧先生春秋经辨序》,六月一日“某既进词业,即其日除枢密院编修官”。爰有后来绍兴八年(戊午,1138),胡铨上书宋高宗,直接喊出“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之豪壮语焉(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三人者,使臣王伦、参政孙近、丞相秦桧是也。
综上所述,“周瑜二十四经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饭”云者,乃好事者摘录自胡铨三十五岁时所作《上张丞相书》内文字,冠为李邦直所言,杂钞入东坡笔记(或即《志林》),赵氏、商氏刻《东坡志林》因之,又为茅氏编入《东坡先生全集》、毛氏编入《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且东坡与李邦直多有往还,诗词唱和,东坡亦曾刻李氏《超然台赋》于石,并跋其后曰:“邦直之言,可谓善自持者矣,故刻于石以自儆云。”故于《李邦直言周瑜》条,迄未有疑之者焉。

茅维编《东坡先生全集》卷六十六(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然则,前人文辞,常互为引述,焉知此语非胡铨借用李邦直者哉!或曰:“若无铁证,只是姑备一说而已。”昔人所谓“孤证不立”者,殆亦此意也。然而,即从语境言,张浚以右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拟北伐中原,故胡铨以“周瑜二十四经略中原”作喻,情状近似;而四十岁时之李邦直,所任之官职,最高不过六品,岂得有“经略中原”之现实雄心也欤?职位不相符也。且“经略中原”盖多为偏隅东南朝廷之战略思维,如东晋、南朝宋、南宋之朝廷与士人,好作此语,尤以宋高宗时为最夥。又按,李邦直四十岁时即熙宁四年(辛亥,1071),是年三月,韩绛因“兴师败衄,罢知邓州”,李清臣受牵连,五六月间,通判海州;同年七月,东坡通判杭州。可知自三月至五六月间,东坡与李邦直俱在京师,两人交好,必有过从。李属于“待安置”身份,或得无所事事,爰有“多睡善饭”云尔,亦未可知也。
古人于苏东坡生日这一天,会举行“寿苏会”。今天(腊月十九)正好为苏东坡诞辰987周年。本篇是《读东坡集札记》(原载《传统文化研究》2023年第四期)前两节,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多注释(含考辨说明),兹从略。征引请以原刊为准。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E-MAIL:dandanxi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