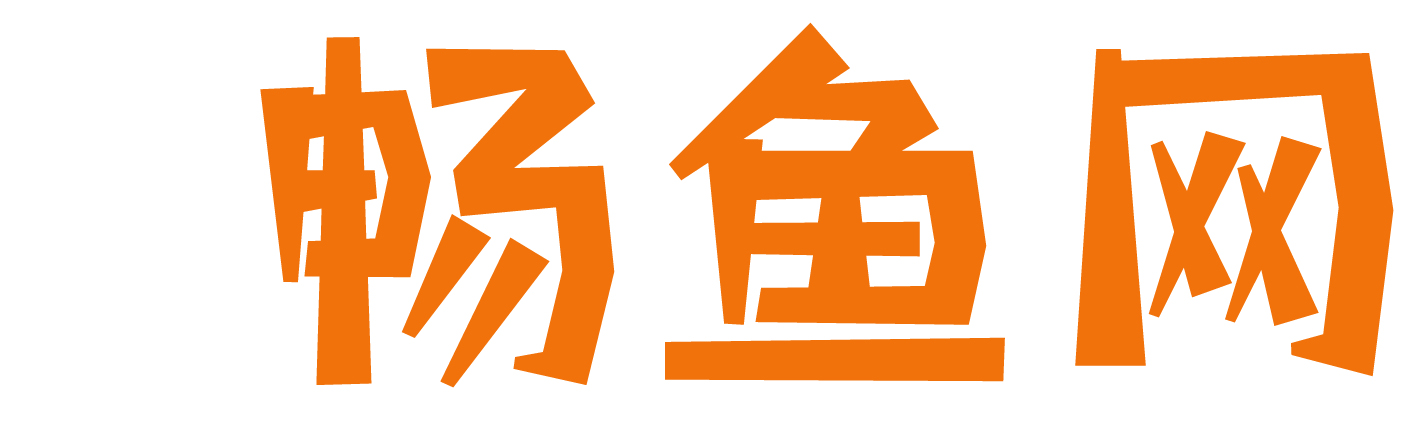这里的“解放”一词并非“解放军”“解放区”中的“解放”,不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或“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解放”,这个“解放”在“文革”中另有含义。与它相邻的词不多,勉强可以举出一个“给出路”;与它相关或相反的词随便可以举出很多,诸如“打倒”“靠边站”“走资派”“下放”等等。和“牛鬼蛇神”一样,“解放”也没什么科学的定义,它代表一次生活地点的“位移”,或一次政治身份的渐变;是“施威”之后的“赏恩”,“大紧”之后的“小松”。这其中的滋味,“解放”过的人才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
在《我写文化大革命》一书中,于光远说七十年代初他在干校曾几次听到“某某被解放了”的消息;他说他为民族和社会解放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之后,竟产生了一种盼望早日“解放”的想法。这可以看作是“解放”的用法之一:被下放到干校,又被允许回去,就叫“解放”。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创造性”地把“解放”一分为二:“半解放”和“完全解放”。季先生说,他感觉到的“半解放”是接到“革委会”的通知,说他可以离开“牛棚”回家了,可以睡在自己的床上了。但是,“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点钱,吃饭也不够”;外来的压力也没有消失,“仿佛成了瘟神或爱滋病的患者,没有人敢接触”。他必须到指定地点参加“学习”,可是,“同革命群众在一起,我还是非常不习惯,有点拘谨,有点不舒服。我现在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
到了一九七一年,季先生觉得自己“完全解放”了。派给他的差使 处”。是看守门户,传呼电话,收发信件和报纸。如何是“完全解放”呢?季 先生说:“我无忧无虑,身体健康。忘记了从什么时候起,又恢复了我的 原工资。吃饭也不用发愁了。此时,我既无教学工作,也没有科研任务。 没有哪一个人敢给我写信,没有哪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都没有,我真是十分欣赏这种“不可接触者”(印度的贱民)的生活,其乐也陶陶。”
所谓“解放”,原来就是多少能过一点正常人的生活了,也可以“偷 偷”地干点自己想干的事了。于光远先生“解放”后过不惯闲散生活,就 自己给自己恢复工作,联系一帮青年编了几本书。季先生做“传达室老 大爷”之余,开始暗地里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晚 上在家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白天上下班路上或传呼电 话、收发信件的间隙,再把散文改成诗;兜里有几张写有译文的小纸片, “闲坐无事,就拿了出来,推敲、琢磨”。季先生说:“我眼瞪虚空,心悬 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我在干什么。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了。”
季先生心中藏无限春光,但外面的世界离春天还很远。林彪摔死 温都尔汗,那“轰隆”一声炸响惊醒了很多人,也“解放”了一些人。 但是,真正的解放时间还没到。“解放”不过是“下放”之后的“上放”, “瓦解”之余的“不解”:头上的“帽子”和心中的“捆绑”,都还紧紧的。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E-MAIL:dandanxi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