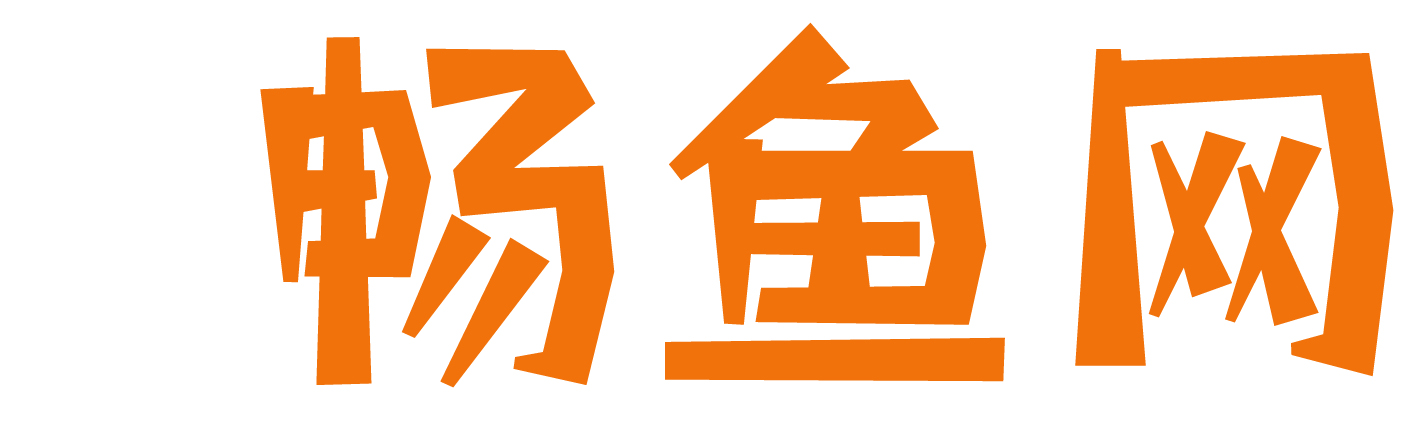“他们既不太独立,也不勇敢。可能就是别人所说的失败者,不断碰壁,但还在拼命地去试,没有放弃。”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全文约8505,细读大约需要18分钟

第六名,成为九连真人乐队在《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抵达的浪尖。这支从广东河源连平山区走出、刚成团一年的“黑马”乐队,看似提供了一个血气方刚的草根励志版本。但他们说,“上山、下山”隐喻的现实,都与浪漫和决然无关。每一步选择里的纠结、疑虑,包含着这个时代阿民们的共同难题。
“阿民是我们每一个人”
三更半夜的连平,夜灯迷离昏黄。偶尔有些狗吠声,穿透大排档和未眠将眠的窗口。
一列鬼火摩托,载着一群少男少女,在街巷呼啸而过。要把车头往前提起,再猛地放下,炫一把。引擎的轰鸣声,“呜吼——”的叫喊和挑衅声,此起彼伏。
这种车子得拿国产小踏板的女装摩托改装,男装摩托就不要了,起步太慢;头盔、手套,自然全无;直通排气是必须的——这样压路而过时,整个街道才知道他们来了;有条件和心思的,再装上点氛围灯——如果不亮,怎么叫“鬼火”呢?
连平人的记忆里都少不了这样荷尔蒙爆棚的一幕。飙夜车的浪荡少年,自以为酷,浑不顾旁人。阿嫲阿媄(母亲婶婶)们苦口劝阻,何曾有效。
“我也骑过鬼火摩托,但不会做那些很危险的动作。”几年之后,写出了《夜游神》的九连真人(以下简称“九连”)主唱阿龙说。在当地方言里,“夜游神”指的便是无所事事,到处闲荡,不务正业的青年。
“当时就想写那样一群人,(他们)就觉得这样天经地义,理直气壮。那我其实是要反讽一把,再青春叛逆,做事还是要谨慎一点。你用纯说教的形式去讲,他听不进去的,会觉得凭什么听你说啊?你又不是我父母。于是就用一个初中生的视角去写了。”
在鼓手吹米看来,《夜游神》既是第一支完整的九连原创作品,也最代表这支乐队的气质。经纪人宋昕薪颇感遗憾的是,位列第六的九连最后没有机会在《乐队的夏天》(以下简称“乐夏”)的舞台上呈现这首歌。
但这个叫做阿民的客家青年,从这首之后,反复出现在九连的歌里:
得知阿诚遇到麻烦,阿民惊惧惶惑;(《夜游神》)
混不了江湖,“毛(没)钱毛着落”,却依然“爱行出去还要行落去”,和阿爸辩驳,又底气不足;(《莫欺少年穷》)
仿佛穷光蛋李三雄的儿子,希望孤身在外闯出天地;(改编《凡人歌》)
人到中年还不曾“出人头地”,只能遥望乡土,哪怕女儿在下雨天眼巴巴地盼着,也只能含泪作罢……(《落水天》)
莽撞、冲动,眼高手低,总蠢蠢欲动,想干一番大事。留在大城市,空无一技;回到家乡?又恐遭人嫌忌。
阿龙说,阿民身上多少有他们乐队三人的影子,也照见了大多数85后、90后当下的境遇:即将面临(或刚刚迈过)30岁的坎,面对就业、返乡的选择——一面是独生子女与家庭的冲突,另一面是苦求而不得的社会认同感。“他们既不太独立,也不勇敢。可能就是别人所说的失败者,不断碰壁,但还在拼命地去试,没有放弃。”
九连真人《莫欺少年穷》
代价
105国道进入广东境内,第一个县便是连平。四面青山,如长长的手臂,将县城掬在中央。从上空俯瞰,东江支流像一道平滑的半圆弧线,将县城和周边的小镇区隔开。
“九连真人”的乐队名,来自他们从未去过的那座秀美之山,也点出了创作的主旨——基于真实的生活。

九连真人在连平的日常生活 图 / FIGURE提供
阿龙和小号阿麦自小认识,趣味却不尽相同。阿麦一直听古典音乐和流行;阿龙很早就爱摇滚,但从前视野里唯有Beyond、五月天、苏打绿,内地的统统上不得台面。
上大学是转折点,耳目被重新洗刷。
“之前就是井底的蛙”,还不要提涅槃,一度把枪花、Mettalica当成摇滚的代名词。“以为一定要有金属riff,才叫摇滚乐。第一次看视频里Radiohead的《OK Computer》,这群人疯了吧,怎么这样去弹琴?!两个鼓手打一样的节奏,吉他的groove(律动)好难听。主唱就像多动症,在台上蹦跳,唱着很飘的东西,加了效果器。完全无法接受。”阿龙在《音悦人生》的访谈里回忆。但那音乐又对他触动很大——不知道为什么微博里那么多国内的音乐人在转发。
反复听,由浅入深。看乐评分析,原来西方摇滚脉络是英美不断交替发展,像螺旋一样。阿龙才明白,从前的自己太片面了。
阿龙读书的成都摇滚氛围浓郁,秘密行动、海龟先生、马赛克、阿修罗这些乐队,渐渐都进入眼帘。受到冲击的他会试着拿单线圈的吉他去弹新金属;听谢帝唱《明天不上班》,“居然可以写得这么实,这么狠!”
《莫欺少年穷》里,“兄弟全部都知道出去”——不论遇到什么,这一步总是要迈的。
毕业后,还没想太明白的阿龙,去了深圳做游戏原画设计师。频频遭受领导打击,他从自我怀疑到终于了解:除了高薪,这行什么也给不了他。夜里踩着自行车回宿舍,只有耳机里的音乐能带来安慰。
过年回老家,他和少年时的小伙伴喝茶、玩吉他,久违的快活又回来了。没几天,微信里蹦出鼓手的一条消息:“阿龙,回来考个老师吧,一方面完成家长的心愿,而且大家可以天天在一起,无忧无虑地生活。”
“哇,一说到这句,马上心就飞起来了,飞回了老家。”他的眸子亮了。

贝斯手万里囤音响设备的仓库成了大家的据点。被唤作“里哥”的万里头发最长,年纪最大,说话却是最细声慢语的那个。
和阿龙一样,万里更喜欢在琴行里教学生:只用面对学生和家长,相对单纯;之前在手机专卖店、电影院和金融机构工作,从穿戴到语言,都要光鲜活泛才能成事,他却拧巴;直到拿租赁音响设备做了主业,闲时和阿龙他们排练,虽上顿不知下顿,但总算回归本心。
至于阿麦,看起来最阳光的一个,迷茫的时间也最短。岭南师范毕业后去阳江教书,日子里总差些什么。三人都笑说他是被阿龙的电话给“骗”回家的。接到发小的回乡邀约,阿麦没多犹豫。“大家老说这乐队小号特别,不过正好是我大学学的管弦乐,赶巧了。”

“回来当老师,内心真的能说服自己吗?”我问他们俩。
“有代价的,我既然能回来,肯定就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想玩音乐。”阿龙斩钉截铁。又说,“头两年我们也是经历了挺多的,放弃了挺多。”
“放弃的是什么?”
“就所谓那种体面一点的工作咯。在朋友面前我说过,我已经注定成了一个,那种所谓回到家、被(长辈)安排生活的人。我们很多朋友还在外面嘛,在为自己的梦想在打拼。”

九连真人乐队,左起贝斯手万里,副主唱兼小号手阿麦,主唱兼吉他手阿龙,2019年7月24日,拍摄于北京SAS酒吧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牵绊
和靠山吃山的客家祖辈不同,阿龙和万里的父母,已脱离了农田,在学校和医院谋职,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家庭。然而安身立命的重要性,始终深深烙在客家人意识里,深信“人唔读书无文化,鸡毛上砰人看轻”。何谓“出头”?怎么都需要一份稳定、体面的职业来交待——譬如老师、医生、公务员。阿龙做过的设计,并不在其中。
《莫欺少年穷》里,阿民面对阿公阿叔阿婆阿伯和阿媄一群亲戚舌战的场景,有夸张成分,但也和生活相差无几。
有年清明节,万里一大家子人回去扫墓。有亲戚问他,学习怎么样啊?还是老样子呀?没前途哟……“他们的口气里,就是把你这人给放弃了。”
一次他们做了个小范围的音乐会,万里的好友也上台玩了一把。“他回家发到朋友圈,领导看到就说,你这个身份搞这个东西,给企业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哦。朋友越想越来气。”很少情绪化的万里,那次也着实失落了一把。
即便是“乐夏”播出两期后,得了好名次的他们仨回到老家,亲戚们依然会殷切地流露:能有更稳定的工作,还是比这个(乐队)好。
一面想奔出去证明自己,一面又被家里强烈地需要。亲情、道义和内心希冀之间的拉扯,温甜又艰涩。不行只能取一头,甘苦,都自己咽。
乡镇里面的医院,工资才一千多,经年未提。好些年前,为了供孩子念书,万里的父母跟人合伙开了饭馆。白天在医院上班,还得抽空给餐馆客人打上几通热络电话:“新食材到了,要不要来尝一尝呀?”
“他们那时都很瘦,脸色也不好,还要陪酒抽烟,应付人情。”起意要买吉他的高中生万里,在饭店里闹过小脾气。可把玩音乐的心思跟父母讲清,父母还是应允了。“一把吉他比一个多月的工资还多。他们只要了解你已经能自己思考、处理,还是会支持。”提起往事,万里有点唏嘘。
“我当时艺考,家里前前后后也投了小十万……”阿龙的回忆也被唤起。
四年前,爷爷离开,暮年的奶奶和患肺病的父亲越发步履蹒跚,万里逐渐意识到责任压肩:“(父亲)老得吸氧,供氧不上来,其他器官也会受牵连。他平时散步走不远,就小走一下。更不用说换煤气,换灯泡这些,都得我来了。”
就这么归乡了。捣腾音响,接零活儿,终究不是老人眼里的“正途”。可儿子就一个,时间长了,也就认了。客家人勤勉坚韧,懒惰就得规训。
“活儿少的时候,我爸看到你在家里太‘清闲’了,就会唠叨一下。一有工作,可能我夜里两三点回家休息一下,第二天六七点就起来了。看到我这么‘受罪’,他就开心了。”万里浅笑着讲。

他们都承认,这代独生子女,对待父母是“既嫌弃、又依赖”。父母把最好的都往孩子身上砸了。儿女既避之不及,又没吃过苦头:受一点挫折就要发(朋友)圈。“再看那时候的微博微信,真是矫情死了。”哥仨摇头叹息。
所谓“下山、上山”,并不径直对应着年轻一代的出走与回归。在阿龙的笔下,那意味着是否对每一件事情做好了准备,想清楚了每个选择要承担的一切。
飞鱼
“林生祥+黄连煜(台湾客语歌手)+董事长(台湾摇滚乐团)+拷秋勤(素材和乐器都源自本土的台湾创作乐团)+Gai”,“万青版的五条人”……从亮相之日起,九连就被外界贴上一串串的标签。
阿龙很有些不以为然:“他们找不到什么可说的了,总需要个参照物吧。这样也好,无法定义我们。”

2019年4月6日,九连真人在黄燎原和宋昕薪为他们办的专场音乐分享会上演出 图 / 逍遥山羊
九连从不自认为“民族”或者传统风。客家戏曲和山歌,多少也听过,但三人始终无感。唯有一次,阿龙被真真切切地电到。
“跟着里哥去农庄的采茶节。一个人声,把所有人的目光和耳朵都吸引过去了。以前我觉得山歌土,可是那个叫谢叔的山歌王真的唱得太好了,嗓音好好听。没伴奏,腔调也足以吸引我,那些急促的音、拉长音,真的只能用‘直击内心’形容。”他好一通振奋——音乐就是这么来的。
回去就搜谢叔,只觉录音版都没有现场的感觉妙。也许听感也需要场域和机缘。但他从此在演唱时,会尽量还原谢叔那样叫人“魂飞魄散”的状态。
但说起台湾音乐人林生祥和交工乐队,他毫不否认他们的烙印。“搞客家语的乐队,都绕不开交工吧。就像任何做艺术的人,他总能找到一个敬仰的前辈,然后往那边靠。”
在交工乐队长达10分钟的《风神125》里,成仔离开村子去大城市打工,一去十年,最终骑着风神125回到老家,一路不停地向土地公和父老诉说自己的无能无力:“母亲这十年日子,我像无主游魂,工作干过一样又一样,哀哉!没半样有希望。女孩交过一个又一个,一概都难以成双。经济起泡我人生幻灭,离农离土真波折,不如归乡不如归乡……”
被城市浪潮淘汰、扔回家乡,又被快速遗忘的阿成,在社会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交工词作者钟永丰看来,正是连接起80年代台湾返乡青年、无壳蜗牛联盟(台湾数年前无力购买房屋而租屋生活的群体)和泡沫经济的缩影。而比起对理论的认知,主创林生祥更在意的是人性与生活,与乡民的交融与实践。
在他们的作品面前,阿龙只觉自己年少时“无病呻吟”的小情绪不值一提。“就好像在大浪的背景下,跳出来的小飞鱼,我就这么跳冒了一下,经不起任何推敲,一掰就倒,也唱腻了。”
于是自《夜游神》发端,他想与那个写过几笔口水歌的自己割裂。“从这首开始,我们就在向交工致敬了。我把《风神125》整张专辑里的阿成,借用过来(笑),对,就是阿民跟着的那个鬼火摩托大佬阿诚。生祥老师写的是一个失意青年回到家乡,我写的是还想往外面跑。他的阿成看淡了人世间不如意,回来是悲凉,或者豁达。九连会更有愤怒感或者冲劲。”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钟永丰与扎根美浓的林生祥,合作了《我等就来唱山歌》等若干专辑。从烟房改造的录音棚,到战队一般林立的菊花田,那时候的音乐生产,自始至终都是“交工”的:农田与野猪就在隔壁,乡亲们热心地送来凤梨与芭乐(番石榴),更参与录音;从录音、唢呐编排到词曲咬合,每个乐队成员都在表达自己的意见。交工的存在与离散、发展,承载了台湾社会三十年的兴衰,也因此具有了历史和文化书写的意味。
九连的阅历与底蕴尚在积累,但哪怕一点点的沉重,到了创作里,也会被见多识广的张亚东劝诫,“还是尽量轻松一些,学会先享受音乐”。
对阿龙、阿麦和万里,表达与享受,或许并非两极——只要一切,发自真诚。
在河源一带,至今,走街的小贩自行车后面都会绑着铁桶,装着做好的油果和叶板,用铁棍去敲铃铛,叮叮当叮叮当。那段时间阿龙听了不少台湾新民谣时期的作品,仿佛回到听妈妈唱那些歌的儿时,“歌词简单又好听,家庭卡拉OK嘛,现在很少出这样的歌了,那我就自己来写写看。”《北风》里的“做事,囊来翻身”,让听到这首歌的客家人淑霞(化名)想起奶奶曾经告诉她的:“人爱人打落,火爱人烧着”(人只有在逆境中才会奋斗)。
“上夜三斤狗,下夜三伯公”的传说在岭南家喻户晓:做泥水匠的李三雄,儿子流落海外不知生死,孤苦过活的他被邻人百般嫌弃。突然一夜儿子中了马票,衣锦还乡,乡邻们连声奉承,连“三斤狗”的骂名都换成了“三伯公”。传说里呈现出的势利和庸碌,在九连改编的《凡人歌》里,正好和李宗盛的“利字摆中间”精准吻合。
九连真人《凡人歌》
《落水天》是为阿麦而写,也是为和阿麦有着相似童年的留守孩子们而写。宋昕薪解释:阿麦从小不在父母身边,委屈或者难过时,会把自己锁在房间哭,脑海里想着“为什么别人可以跟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我却不一样。”
长大了的阿麦早已释然。外公外婆和其他亲戚的关爱与照顾,把“留守”的孤寂冲淡了许多。但一年前在深圳的live houseB10唱《落水天》,他还是没把持住。阿龙在一旁唱着“转来哩哦!”阿麦回应道:“回不去哦。”演出结束,他死活也不想再唱这歌了:“阿民”的女儿如何恳求都换不来父亲回家的决心,该有多绝望?
听到《招娣》,祖籍河源附近的淑霞说心里会有点生疼。“姐姐和妹妹加上我是三个女儿,弟弟是我爸爸从农村‘买’回来的,因为客家人很看重传宗接代。我爸去旅游都只带着我弟,不会带我妹……不仅是我爸妈,家里的男性长辈都基本把女人当生殖工具的。”她因此觉得,九连歌曲里传达出的内容和精神,在当下太稀缺。

贝斯手万里接女儿放学 图 / FIGURE提供
引流
田埂间给乡民演出,听起来诗意浪漫,却知音寥落。窝在家里练,到底动力不足。
阿龙很羡慕本地的街舞人,他们会义务教学校的舞蹈社团。下了晚自习,高中生们在公园里集体battle。“那氛围真的特别好,唯独乐队就没有。没有北方话说的‘茬琴’。”
半年多前,看到“虾米滚石原创比赛”的消息,阿龙帮大家报了名——就想激发下几个人的斗志。
他回忆在成都写《夜游神》,就是车上半小时的工夫。从用客家话创作,到录音,统统即兴。上“乐夏”时气口切得准,其实开始也没多想。“最早的版本里,语言有点杂乱重复,我还有点打顿(磕巴),但那才接近真实的讲话状态。就连电话声,也是用纸包着我的嘴巴,做扩声器模拟出来的。”因为觉得不够好,这个版本已经被他们自己下架。
可参加虾米比赛那会儿,实在没条件,有点滋滋啦啦的《夜游神》录音带,就那么递到了海选评委的手边。
“第一回听,嘿,够乱的。这都什么呀?真没觉得怎样。”在“乐夏”里资助他们贝斯的张天罡说。台湾音乐制作人颜仲坤和吹米却听出了别样的意思。“有点好玩儿,要不给个机会?”
到了广州的复赛,吹米在场地外头小店买东西。忽然听到一阵吉他,账都没结就往场地里头跑。“我说,诶,这应该就是九连,阿龙的音色太有自己的特征了。赶紧先冲回去听一下,完了再跑回来结账。”
到决赛,九连真人最后一个上场。张天罡惊着了。
“听了很多歌,总会养成听觉习惯,但《夜游神》完全打乱了你的预判。阿麦穿了一个帽衫,口袋里还放了个手机,我当时想,居然这样就来比赛!歌的结构变化很大,加了一段普通话,还有最后阿诚的结局,歌的结尾,唰地停了。demo还真有欺骗性。”
评委也对九连的表演印象深刻:阿龙和阿麦分立舞台两侧,像说唱,更像角色分明的戏剧表演。两人用手指天、“怼”地,踮脚,晃肩膀;阿麦的一双眼直往外喷火,仿佛要宣泄出积攒了20年的不平不满。唱到高潮处,阿麦晃头的频率加快,嘴巴张大,那份魔性,让郝云直言“起了生理反应(肾上腺素激增)”。

九连真人在虾米滚石原创乐队大赛 图 / 李奔跑
比赛期间,九连真人便引起了宋昕薪的注意,她把乐队推荐给了老板黄燎原,立誓要给他们做经纪人。久不问江湖事的老黄也动了心。“九连不是文艺青年,也不是纯农耕的写实者,但他们很有点老摇滚的意思,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他说阿龙很像当年的梁龙,轴,演唱起来还有种常人不易察觉的“妖气”。“他可能没有丰厚的知识,但想问题会很深入,所以呈现出一个表面,似乎没那么开心。但一旦开窍,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来。”
不过这份冷静多思,算上阅历略丰的万里,到了人精起堆的综艺和真人秀,也成了被耍得团团转的“小白”。《乐队我做东》的摄像机,老实地记录下了这三人的生涩,玩游戏时的不圆熟,被臧鸿飞和马东挖坑提问时的迟疑,不知所措。阿麦干脆缴械:“我以为今天来,就是好好吃顿饭的呀……”
也是到这时,大家才知道,万里是节目期间第一次参加国内的音乐节,阿麦也是在“乐夏”才尝试“跳水”(摇滚乐手和乐迷兴奋时从舞台上跳下人群,由观众接住再传回台上的动作)。
一夜成名、横空出世,好像能拿来形容九连真人的际遇。阿龙却觉得不然。
“乐队还是正常地生长。其实,我们引发的关注还不到‘中国有嘻哈’(当时引爆)的零头。”细水慢流,在几个人看来才是真实的反应。他们觉得,“乐夏”的热播,最积极的结果是引流来了一部分从来没有听乐队习惯的人。“给很多人打开了一个口子。还有就是,对那些快要放弃了的乐手,(要相信)他们自己就是夏天。”

村里的阿姨们觉得九连真人为家乡争光了 图 / FIGURE提供
“乐夏”最后一场,白岩松语重心长地寄语,九连单位的领导应给他们几个升职加薪。阿龙没妄想这个。从开赛到完赛,乡里乡亲投在九连身上那股好奇和猎奇的眼神,和几年前打量他们时并无分别。“没想到这样也能够成名啊?就这种心态。我们也不希望在当地造成一个多大的影响力。能少点偏见就挺好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比那些只爱打牌,一味喝酒聊天,会好很多。”
阿麦和阿龙的学生们自然会追问两人参赛的点滴,可到了课间,孩子们还是爱刷抖音,偷偷打开电脑听《学猫叫》或者喊麦。“还问我,老师,你在大厂,有没有见到那个谁谁谁(流量明星)?呵呵。我都不知该说什么。”阿麦一副抱歉的表情。

阿麦在学校办公室 图 / FIGURE提供
阿龙曾经放Beyond的《Amani》给学生听。孩子们嘲笑他老土,他便细细解释歌曲的时代背景,“amani”和“nakupenda”在斯瓦西里语里的涵义(和平与爱)。“有的不太明白,有的还是点点头,对他们当时来说可能不会产生什么巨大的影响,但我相信,知道总比不知道的要好。”
也有些少年,在连平街道上看到阿龙,不太好意思打招呼,会到县城里跟他去聊比赛。“问我,在连平还能不能找到人来组乐队?我说,是可以的。我会告诉他,还有哪些学生在玩,他们刚好又在同一个高中或者初中,那你们就会有伙伴了,这个群体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结束一天的排练,收工回家 图 / FIGURE提供
对二手玫瑰曾经的期许,黄燎原又一次放在了九连的头上:“希望你们不仅仅是做支乐队,而是能进入中国文化史。”
“这个词太大了。”阿龙回应。“他跟很多人都说过。我们可没想那么远。就想着能把‘阿民’带出去,见识一下。”
问万里,演出费涨了好几倍,是不是能把买音响的欠债迅速还掉了?他正要点头,又嗫嚅着,“说不好,也许还会再投(钱)进去。好设备好多呵。”
这或许是他们未来面临的头一个落差。在“乐夏”,所有的灯光音响舞美,都为参赛乐队度身定制。编cue(灯光控台中用于所有编程数据的基本占位符)时,灯光师对场景做了独特的处理,会用“燥、静、甜、热血、情怀”等等分别展现每支乐队的表达。
“你的感官感受到的一切,都是专业人士精心准备、不断调整出来的。突然回到家里后,那么简陋的环境,包括以后的演出,也不一定有这样的配置了,就是live house的氛围。当然,有氛围,就不错。”阿龙说。
创作上,困扰他的就是视野。“现在还是太小、太窄了。我希望有更多的可能性,不单只是坚持客家话、或者加入普通话,语言从来不是个问题,你有话要说才是重要的。”
“越唱到后头,越有不少听众觉得曲风有点单一?”
阿龙坦承,好多想法,乐队因为硬件和人力都没法实现,自己不会的也很多。“各种采样的再创作、电脑制作,都不擅长。要学。”
“真的不打算离开连平?”无数人问过,阿龙的回答都是“不会”:家人要照顾,北京的熬夜节奏难以消受;更何况,没有连平,没有当教师、街边地头的摸滚,何来九连?
黄燎原倒付之一笑,祖籍梅县的他送给九连自家的家训,“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以前的中国农民,哪怕到西伯利亚也撒两把种子,看能不能长庄稼。如今大城市的早没有这根性了。但客家人还是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对九连来说何尝不是,到哪儿,都能变成家乡?关于未来,不管他们,还是外人,都没必要太早下结论。”
(参考资料:音悦人生访谈。感谢李磊、张薇、陈雅峰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肖淼、都芃、李健祺、郑伊灵、苏碧滢、刘梦婷等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
提供有格调、有智力的人物读本
记录我们的命运 ·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E-MAIL:dandanxi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