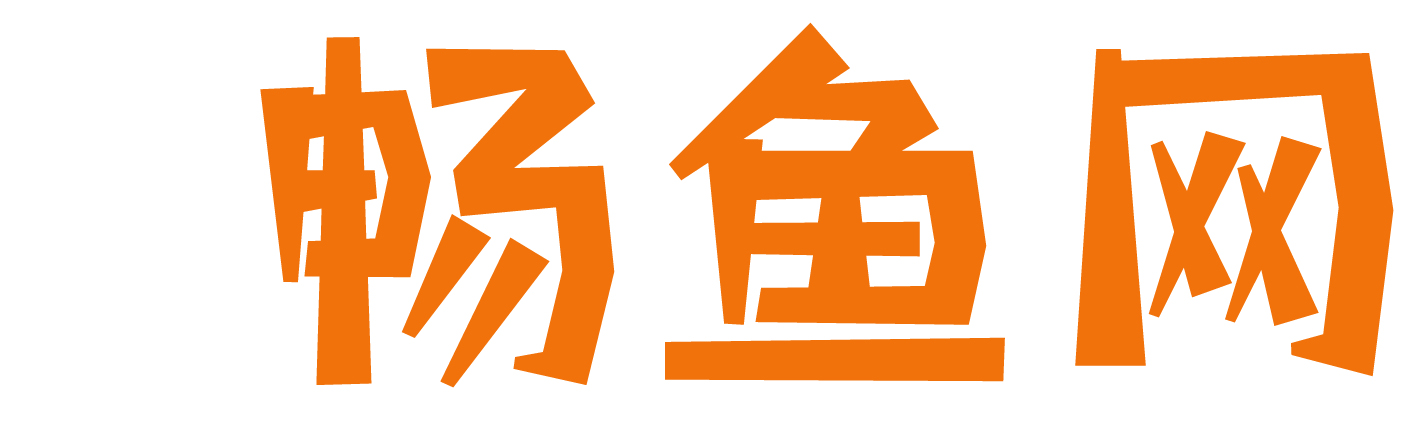1
广州下雨好生猛,从遮天蔽日的绿盖缝隙漏下,像一个个箭头折断在沥青马路上。这种雨淋了要生病的,母亲说。
她一只手撵我的书包,进去便利店。“刘师奶买嘢啊?”白发老婆婆脸上沟壑加深,接过母亲用力抵住的门把手。“系啊系啊。”母亲寒暄。我的粤语比母亲好得多,用手点她湿漉漉的后背:“妈,几时我地再去澳门啊?”
“得闲就去咯,”母亲把手搁在我头上,“你老豆宜家系澳门做生意,几时去都得啦(你老爸现在在澳门做生意,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啦)。”磕绊的乡音,空气间隙藏了一朵微笑。在老家,新广州人的身份使我们自豪,到了广州,要做新澳门人才能挺直腰杆。
“下次我要去赌场!”我尖利的愿望没有突破重重声浪。
一个男孩蹭过我右肩,抱住老婆婆的腰,“嫲嫲,想食朱古力……”薄薄的鼻梁,一双黑眼珠透过玻璃片儿,有点斜视。他眼中的敌意,让我手指蜷缩。
门又响了,进来一对兄妹,头发湿得黑透,贴在发亮的白皮肤上。女孩从货架上抽出一盒熊仔饼干,蹙眉像欣赏红酒。她将货架翻乱,男孩又随手整理。咚!两玻璃樽汽水立上收银台,他拿下挂在雪柜壁的开瓶器。我忍不住探头去认那牌子,只见大颗水珠从瓶身的花字滚落,如女孩发梢晶莹,短发下,后颈绑了一个小小的羞涩的结,像一只红蜻蜓,红色的胸衣若隐若现。女孩从校服裤兜捏出濡湿的纸币,用国语说:“你好,买单。”收银台后的男孩,始终打着电动。
戴眼镜的是猞狸眼(斜视的人),那两个好看的是李英德和印小柔。他们原来不是兄妹。还有一个角落里的肥佬。我中学最好的伙伴,几乎都在雨天的便利店见第一面。
“刘展凯,老地方见!”他们对我说,只有印小柔叫我凯子。她小时候在台湾待过,闽南语骂人很溜。我们都跟她学:“干你老师啦!”大家彼此相差一两岁,却在同个社区同间学校同个年级。社区大榕树后这家新开的便利店,原是肥佬他爷爷开的士多(店铺),他大伯找人加盟又翻新,就成了社区首屈一指的便利店。明亮的货柜,滚沸着时髦的关东煮,满雪柜印着日文的朱古力雪糕酸奶便当,汽水的种类也多,储满15个印花能换当季最潮的文具。满满当当三排货架后隐蔽着两套餐桌连体椅,散着汤渍和扑克牌,上班族不屑与我们争,老人见了会皱眉走开。这就是我们的老地方。
2
七点过十一,我还未出家门。母亲深陷沙发椅里,两只眼睛也深陷眼眶,像干涸低落的河床,弟弟看见,肯定要说:“她又发癫了!”父亲上一通来电不知讲了什么,总之我放学,已见这幅场景,把书包挂上墙,松了劲的手臂变成两挂蔫了的香蕉。明知她不会应,我还是说:“妈……”秒针一格格跳,母亲双眼充盈了泪,我想起往浴室放水的数学题。她的嘴角终于有了纹路,索索地发抖,用家乡话说:“大弟,妈没法活了……”我认命地点头,去厨房盛一杯温水来。母亲摆开我双手:“你爸在澳门有女人,你知唔知啊?成日就知去便利店鬼混!”比起母亲的伤心,更让我伤心的是她粤语的蹩脚。等晃过神来,她又要逼问还让我打长途电话了。
“你屋企果个煤气又点啊(你家那个煤气罐又怎么了啊)?”猞狸眼从暗处伸手勾我的脖子,个子太小显得吃力。推开便利店玻璃门,他窜到货架前选了一包奶酪棒,我跟着付了钱:“喂,肥佬,拿东西。”我在这存了几条烟,每次来肥佬偷偷拆成散装给我。猞狸眼不抽烟,倒是把糖果吃成了个人标签,总能看见他嘴里叼根小棍,吃完还要拿它吹口哨。我拿手干搓脸,看见这副模样,猞狸眼先替我叹气,他老母有双相情感障碍,同病相怜也是我们玩到一块去的理由。
“我真系唔明,有病点解唔去睇医生?!”我大发脾气,在肥佬的底线内踢蹬桌椅,猞狸眼讨好地往墙壁贴当季水果茶的广告,肥佬偶尔从不停机的电动里抬头,抽空帮他大伯卸货。过一会,门响了,是李英德。他从雪柜里拎出两玻璃樽沙示,轻车熟路开了瓶盖,一支自己喝,一支摆在桌上,等人付账。肥佬又从我那些烟里拿出一根,递给他。这败类。偏偏他好看,人又轻巧,使我每次见到他,就感觉自己低了一头。“边个老母又发神经啊?”他把脚架上凳,整个人软软地往桌边靠,脸和脖子的汗像莹光波浪,微微地起伏。
李英德一来,猞狸眼就开始吵了。他们一会说英语老师的衣衫好暴露,一会说蒙面超人的最新手办好样衰啊。我听了一阵就忍不住了,蒙面超人再样衰也比面包超人好吧。我们又一起点评小腿粗壮的挑笔记本的低年级女生,还有粉红头发的平胸不良少女,猜她今天是不是又吃大根。直到印小柔抱着她的平衡车冲撞进来。便利店白光下,她的眉眼浓黑,是老家国画班的回忆,天气越蒸腾,越黑白分明得晃人。印小柔对这烟雾缭绕皱眉,水墨动了,我仿佛听见里面小桥流水潺潺。她付了李英德赊的账,又把喝完的玻璃樽怼到角落啤酒箱里。
我说,抽烟喝酒是我父亲教的,是一种交朋友的手段。所有母亲厌恶的,父亲都鼓励。有一个在澳门做生意的父亲,是我在这里的社交名片。不知道讲什么的时候,就讲对外界的向往。那个外界,通常是印小柔温馨童年中的台湾,和我光明未来里的澳门。去一趟澳门,只需坐船就能到。进去赌场,却要一个漫长的成长。但谁都相信,那是我唾手可得的。为此,我可以长期忍受异地父母的撕裂。金光闪闪的澳门赌场,穿过了未来,用聚光灯把我的头顶照出一片晶莹。那里有丰满的金发尤物,小山似的精致筹码,大智若愚的点金胜手,还有坐直升机般大起大落的人生百态,在每个午夜闪回。便利店变成一个饱满的荧光幕,桌上薯片虾条飞得到处是,大家一口一口吃下身体的躁动与思想的不安。
电话手表响了两声,男孩梦碎。猞狸眼吐掉糖,风一样走了。我们都习惯了。李英德提议,看谁能不用手,最快把上衣脱掉。印小柔没听见似的,跑到雪柜拿一盒速食玉米浓汤,浇了热水。等汤好的时候,她用手机放起音乐,谢霆锋的《玉蝴蝶》,她常听这个。李英德笑她:“老土怪物。”印小柔专心对着慢慢变热的浓汤发呆。很奇怪,她和其他人不一样,不用白色的蕾丝,或者闪着小亮片的嘴唇,无性别的校服正好说明她的好看。我在心里把歌词翻成字,看她白净的手臂支着小脸,突然学到一点寂寞,我猜想印小柔也需要有人把她当作一只玉蝴蝶。这时谁也没说话,便利店冷气开得太足,仿佛要把我们热腾腾而无聊的青春雪藏在这夏夜。
3
便利店鲜少关门,有一回是为了肥佬。两个同级生笑他是寄养在大伯家里的孤儿,他就和人打架。
听到消息时我还在踢球,去的路上已想好,远远看见两三个缠斗在一起的,就不管不顾挥了拳头。本来有我和李英德加入,胜算很大。可他只和别人扯头发:“打人不打脸!”不知道这家伙是来和解还是打架的。我一开始手还是软的,挨了两下之后,火就上来了。因为个子高,能钳住对方的手,我一直占上风。这时我看到肥佬用手肘猛击别人的胸口,这不是下死手吗?无意间,对上他烧红的眼,我不免呆住被人往鼻子揍了一拳,鼻血还未流出,有人领着教导主任来了。
我们赶紧鸟兽散,临走时看见印小柔从人群中投来担忧的目光,我的心脏在身体里咚咚跳。“我教了廿年书,打架的学生就是最坏的!”教导主任还未说话,我们的班主任已经气极,口水对外喷。猞狸眼像老母鸡怀里的小鸡,站在她身后。虽然知道猞狸眼向来(是)乖仔,我还是有点恨意。他眼里只有他有病的老母,可有我们?终究没逃过一个处分,我们在医务室涂酒精,大呼小叫,又被罚去扫空的课室。
空课室在顶楼,灰尘大得掩住口鼻都能闻到,我拿扫把比划两下,发现尘埃居然在暖光中漂浮。窗外一个咸蛋黄,正扯带大片倒泻橙汁般的火烧云,重重往下坠。印小柔开声,把我拉回灰尘里:“其他人呢?”“他们扫别的楼。”一开口就呛得我咳了两下,见她没反应,只好憋住喉咙里的痒。
印小柔问我为什么打架。我告诉她,我有个弟弟有轻微智力障碍,现在在老家治病。小时候,为了弟弟和人打架,虽然两人都被狠揍了,却是虽败犹荣。肥佬是我兄弟,不管他要揍谁我都不会袖手旁观。印小柔不出声,我们并肩坐在一张废弃的课桌上,看她的一双小腿在底下轻轻晃。我没敢说的是,弟弟从未和人打架,他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我也没说,那一年看见弟弟被人骑在地上,我下意识的反应不是上去揍人,而是赶紧跑掉,有多远跑多远。肥佬的红眼睛,使我想起我弟温顺忍耐的目光。这时,旁边的人对我的脸啄了一下。
这样的吻,对一个人来说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但我是个男孩,只想要更多更多的吻。晚上,肥佬因为脸上破了相,他大伯不许他到便利店吓人,索性关张一天。他沉默地跟在大伯身后。我借口怕人报复,送印小柔回家。李英德猛一抬头,双眼在我们身上砸下了锚,铁钩子把我们的小秘密划得破碎:“你地去边啊?(你们去哪里啊)”“送距返屋企(送她回家)。”我不耐烦地拿手摸脸,这时候他知道着急了。“你地想做乜(你们想干什么)?”这四六不通的家伙。忽然,李英德踢了人行道上的共享单车一脚,脸涨得通红,但仍好看。我立马又想打一架。印小柔跑去他耳边说了几句,回来只对我说:“走吧,不要管他。”
我们往前走,听见后面单车被人猛地推倒在地的锵锵声。本来,和他对峙使我有几分愉悦,像苏打水冒泡。晃过神来,却充满了后悔。这样像孩子的吵闹是我最讨厌的,为什么不学会像个大人解决?又为什么制止住他的不是我,而是印小柔?一路上,印小柔沉默地推着平衡车,走到一处灯光昏暗的巷落,我按捺不住把她推到墙上。她没有回避我的吻,我便把手伸进她薄薄的短袖里。我用手握住印小柔,感觉她在我的手掌心颤抖,从未觉得,一个人的汗有这么地让人激动。外面,蝉鸣在扩大,塞满了耳廓。她的胸衣好像儿时大白兔奶糖外的一层糯米纸,被我轻轻揭掉。
那时我并不知道,那正是一个人最容易被爱上的年纪,从旁人的眼光看,青少年是直来直去的螺丝、汁水充盈的植物、感官发达的动物,身上多得是荷尔蒙,还未发出酸腐的人臭味。
4
我和印小柔的暧昧关系没有维系很久。我想她会希望在特殊的节点发生点什么。节点快来了,母亲回老家照顾弟弟,在我独居的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八号风球将登陆汕尾,预计会波及广州。一天下来,天色都很晴朗,我在心里幻想一场盛大的台风。傍晚,我叫印小柔到家里来。挂完电话,连打几个寒颤,我心里恐惧大过期待。
她来了,穿着宽大的校服,熨得平整,像无风无浪的海面。我们在沙发上接吻,门窗都紧闭,冷气机在头顶发出长吁,汗水在失掉边界的身体上交错,酝酿荷尔蒙的意外。我揉搓她的身体,把脖颈后那个一见钟情的蝴蝶结解开。印小柔轻轻拍掉了我的手,像一种玩闹。正当我的右手往下渐渐深入,她突然一把握住了它,准确得像青蛙对猎物弹出舌头。
“不可以吗?”“不可以。”她摇摇头,鬓边的汗坠下,滴在我心上。为什么?我一定把吃惊写在脸上,所以她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我的双眼说:“别的可以,最后那一步,不行。”“你害怕吗?”我摸摸她的手臂,软化的语气近乎哀求,“哪里不舒服?”“没有不舒服,其实挺舒服的。”她看向窗外,那里乌云正像织毛衣似的越织越厚,阴天衬出她神色冷冷的,一种艳丽的冷,轮廓也是不由分说的锐利。我忽然明白自己想错了。印小柔心里分明有一道红线,有的亏可以吃,有的亏绝不会吃。她一直是个谨慎而早慧的女孩。
我跳起来,把短袖穿上,用手拨了拨头发,问她要不要到卧床上看电视节目。印小柔没说话,嘴角往两边拉,在沙发缝隙里拽出她的胸衣,两条带子在漆黑的短发下,打了个高昂的结。见她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不免气顶上胸口,一边用手打她的背,还有手臂,发狠赶她走,一边忍住眼里的酸涩与不甘。外面轰隆隆,台风正无限迫近我们,不时有一瞬闪电把阴郁湿热的屋子点亮。
印小柔大概被我吓哭了,或者没有,我也不太记得。总之把她赶跑,我又疯了一样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打开,冷气机声立马被盖过。呼——呼——风从四面八方猛吹进来,由客厅流动到卧房,在屋内肆意翻看施暴。还有莫名其妙的尘土、棉线、羽毛、手掌大的叶片,统统飘来,洋洋洒洒留下记号。客厅木制的杂志架倒了,我房间的CD也从书柜上跌落数张,厨房传来劈劈啪啪声响。呼——呼——风很强,却无法贯穿我,只是把我两边耳朵勒得生疼,每一分每一秒都后悔,我如此一览无余,被她如此清晰地拒绝了。我在一片狼藉中安慰自己,一次又一次,直到整个人几近涣散,一点点乳白的泡沫涂上木地板,画不成形的图案,空气内重新填满了一种新鲜的腥臭味道,才恢复感知。家里,到处湿答答的落雨。朦胧中,瞥见远处碗大的棕榈被横风拦腰劈断,我一下惊醒。
外面的世界七零八落,不知道印小柔是怎样回的家。我感觉好可悲。相比起她的早慧,我只是一个晚熟又早衰的人。
台风天后,人们踩着街上断裂死去的树木与花,继续返工上学。我每晚到便利店报到,心里那只靴子始终没有落下来。印小柔和李英德没再如约出现在便利店,一齐消失在了外面的世界。有时候坐在店里,猞狸眼突然把放了口香糖的汽水对着我猛射,我在笑骂招架中,也会想起那两个好看的人,不知道这个时点他们正在做什么。从前我们曾讨论,便利店为什么总是这么亮,李英德说:“憨居(傻子)!因为白炽灯嘛!”“屁啦,教室就没有灯?”印小柔答他。我认真地想,教室那种亮,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茬茬收割少年人的明亮与水灵,修炼一室青烟缭绕,让人昏昏欲睡。而便利店的亮,是糖油混合物,会迭代的便当与饮品,日日新月月变的优惠广告,像我们的未来一样,是充满变数的希望。
多年后印小柔和李英德结婚,我掏光身上所有钱送她一块手表。她说拜我所赐,那个台风天,是她人生中骑平衡车最快的一次。
5
我不懂经营不善的意思,只是临近中考那一个月,便利店优惠花样特别多,终于贴出了一张粉色转让告示。它对别人发出邀请,也对我们提出拒绝。便利店不会永远明亮下去。有人失掉了乐园,有人失掉了继承家业的出路。我们在一次次的被拒中演习成人世界的功课。
为了前途,母亲对我耳提面命,也许像他们说,我们是蜜罐里养大的一代,吃读书的苦是不容易的。日出(后)每一天都是新的,脑子里的知识依旧空空如也。为何考试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我看见周围都是陷阱,却身不由己踩进去。每天夜里,扣上房门就睡得不省人事,到了白天,一面张大感官贪婪娱乐,一面在悔恨中把精神消耗殆尽。
直到中考成绩公开,我的零用钱被停掉,失去了鬼混的资本。可这时,我终于得到了一次进赌场的机会!小舅舅到澳门找工作,我知他为人贪玩,便拜托他。他说我长得高,问题不大,先去赌场,再见我父亲。
我整夜不睡,去到澳门,过关和坐观光巴士都不是第一次,这回却带着全新的目光,怎么看怎么兴奋。听人家说,新葡京酒店的外观是一朵盛开的莲花,我却觉得像一位披甲执锐的古代战士,已准备好上阵冲锋。那条街上,走两步就有取款机与当铺,走十步就有一家新的娱乐场,给我极大震撼。
澳门当地不爱说赌场,只说娱乐场,进去之后我才晓得,里面购物、影院、酒吧一应俱全,装潢得金碧辉煌,男男女女搂抱着走,我只把自己的眼睛当录像机使。兴奋不容许我放大细节,比如天花板斑驳的金装,灰得失去品相的毛毯,巨型水晶灯的款式老土,某串灯泡早已不亮了,还有穿拖鞋短裤的邋遢游客,像我一样望也望不够。我在心里小声说,再考究的梦境也有过时的一天。
喏,小舅舅喊我,给了五百筹码,捏在手里只五枚塑料片。每一片,黑色圆圈内,有三朵太阳花簇拥着数字一百。没有多余的,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四下里全是赌台,比桌球台子略大一些,上面挂细长的彩灯,像一只色彩缤纷的大蜘蛛爬在台上。荷官并不全是美人,也有干瘦的老头,女的也有四五十岁的,浓妆盖着憔悴的眼和皮肤。不同赌台押的金额不同,我眼巴巴看着一万甚至更高的,只敢混在最低的三百的台子周边。这里的人也不少,脸孔普通,都在大呼小叫。骰盅盖着三粒玲珑的骰子,比大小。“十以下是小,十以上是大。”小舅舅教我。我学着人,把三枚轻飘飘的筹码叠上去。我赌大。然后一开,是——“小”!荷官拿小棍一敛,我的三枚筹码瞬间坍塌,和其他大片面目模糊的筹码一同归人了。我简直把下唇咬破,手里的大半筹码就这么没了。“还能押点球,单数,双数,总数,还有每个骰子的点数……”小舅舅对着我笑,附在耳边说。我难以定神,猛地听见自己心跳,极快的,咚咚咚,咚咚咚。在人群的嘶吼中,押了一次单数,又押了一次双数,我的筹码输光了。我转头望向小舅舅,他嬉笑着给我看空白的手心,喊道:“Game over!”
这时我简直想哭。就这么结束了吗?一切都和我以为的不一样。美人呢?会把扑克牌叼在嘴里的邱淑贞呢?西装笔挺又料事如神的赌圣呢?花花绿绿用也用不完的筹码呢?我甚至连一张椅子都没有!待了不到十分钟,我就被这冷酷而残旧的成人世界踢出去了。
走出赌场大门的那一刻,我还搞不清状况。有雪糕车经过,我问小舅舅买一支云尼拿雪糕吃,他摇摇头说:“本来你刚才可以赢的,赢了你就可以花自己的钱买了。”这一次,我的眼泪真的掉出来,偷偷用手指抹去,心里变得一塌糊涂。
上了车,小舅舅带我去见父亲。在父亲办公的地方,我见到了他“另外的女人”。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大班桌后,对一份摊开的文件喋喋细语。那女人和母亲不是一回事,古铜皮肤,锋利的紫色嘴唇,双眼外缘有一道浓黑的线,一身瘦瘦的职业装。弄明白我是谁以后,她眼里有一瞬的审视,又转为看父亲的柔情,我就意识到她是谁。“咖啡?”她提起桌上的杯子,父亲便点点头。那女人不看我们,走过去,留下一阵个性浓烈的香水味。我也故意扭过脖子,看窗外。澳门的天总是晴转阴,一点点雨被风刮上玻璃,慢慢地,落地窗变成了一大块透明网眼布。父亲问我们赌场好玩吗,他审视我的眼神比另外的人更加可恨。我不愿意说话。小舅舅得了命令,带我四周转转,吃点东西,我们便离开。从办公室沙发椅取走我刚放下的背包,背回身上,它还是温的。
出走廊的一瞬,我想躺下,想撒泼打滚,没想到,愤怒在盛开的一霎就枯萎了,像蜷缩无力的花瓣,风带雨地从门缝漏进来,不断扑在我身上。“带伞了吗?”小舅舅问,我摇头,他说那就快跑一下吧。乌云在头上煎熬,我想,这个世界对我们有太多的教育,唯独缺少了爱的教育。“但是擅自对世界抱有期待是不礼貌的。”我自言自语,用手指摸跳跃的雨点,柔嫩得像新生儿的眼泪。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往前跑,还是往后退。
夏天的雷阵雨忽而过去了。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E-MAIL:dandanxi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