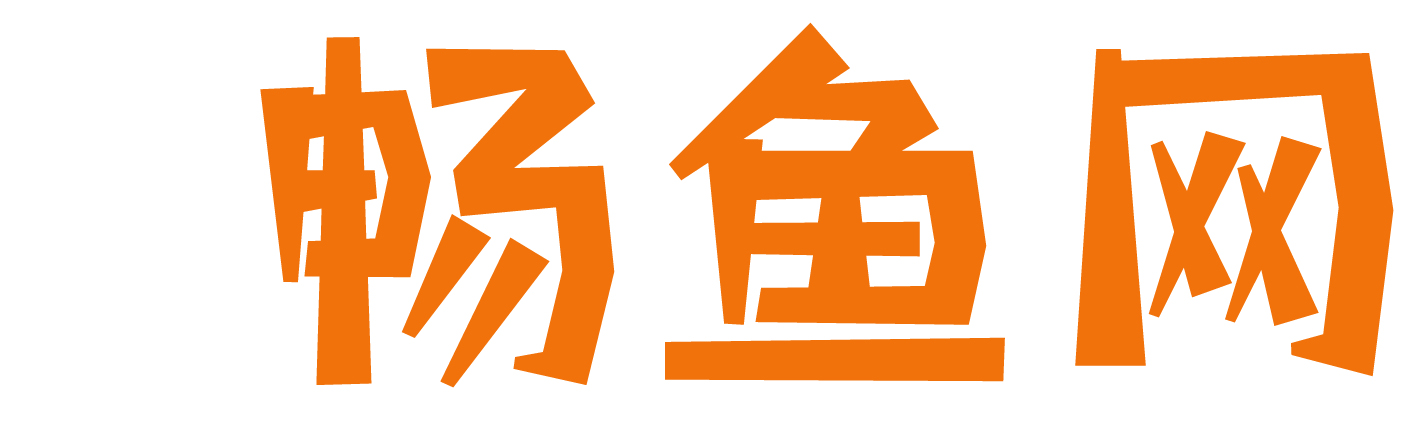《儒林外史》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

对科举和八股文的声讨和攻击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讽刺文学力作。参透人世虚空的吴敬梓,对摧残人性的科举制度与八股文写作发动了一场最全面、最猛烈、最坚定的文字声讨和抨击,气势汹涌如潮,提出的种种尖锐而有价值的问题仿佛巨石入水,在整个封建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全书能“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像物”,因而使得“擅魅翅烟,毕现尺幅”。
《儒林外史》共55回,约40万字,描绘了近200个人物,以十多个既独立又有联系的故事,细腻地刻画了一群追求功名富贵的、各种类型的封建儒生和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剖析了当时读书人鄙陋变态的灵魂——数十载寒窗只为考取功名,人们心理变得麻木、丑陋、愚昧,灵魂扭曲。而一旦他们如愿以偿,跻身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作为既得利益者,便继承前任衣钵,媚上欺下,鱼肉乡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
《儒林外史》是写儒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儒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是官场的世界。这是一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暗的书。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对儒林阶层进行了无情地鞭挞、含泪地批判,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系列深受科举毒害的迂腐的读书人、虚伪的假名士,也塑造了理想中的儒林人物。虽然假托明代,却是封建社会一幅真实的生活画卷。
这部书中的人物形象,截然分明地分成两类:一类是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腐儒,他们丑态百出,是作者讽刺和揭露的对象;另一类是对科举功名丝毫不热心的真儒,他们磊落风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和希望。在作者看来,儒林中的种种丑恶,均源自对功名利禄的追逐,并因此而丧失操守。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真儒、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前一类中的理想人物是王冕、杜少卿、沈琼枝、庄绍光、迟衡山等,后一类的代表人物是市井“四大奇人”。
全书的故事情节虽然没有一个主干,却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为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吴敬梓不仅写出了科举制度外在的种种弊端,并且将他锐利的笔触深入到为科举制度毒害、折磨的人物被扭曲的灵魂深处,从而使《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作者现实主义的冷峻目光,始终不是只看到一些孤立的个别的人,而是投向整个社会。他从社会环境来写人物的命运和性格,又从人物的命运和性格来表现病态的社会。
我们从书中的故事里不仅看到了独具性格、面貌不同的人物,而且看到了一个腐朽堕落的、光怪陆离的社会世相。作者对那些热衷功名富贵以致中了邪魔、被社会挤压得灵魂都变了形的卑微可怜的儒生们,既作了无情的尖刻的嘲讽,又表现出关切的哀怜和同情。而为了改良社会,表现作者的理想,吴敬梓在作品中也塑造了几个正面人物,对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给予歌颂,对不迷恋科举的读书人加以赞扬,把希望寄托在用儒家的道德规范来扭转颓败的世风上。这在当时,有着鲜明的现实性,对后人也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吴敬梓卓越的幽默讽刺才能和驾驭语言的本领,使《儒林外史》取得了极其出色的艺术效果,在讽刺文学中具有无可争议的崇高地位。作为一部形形色色人物的“灵魂史”,它开辟了一个视野,提供了一种眼光,形成了一种手法,创造了一种小说结构形态,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杰作,构成了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又一高峰,在中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超越的价值。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自称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他出生于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曾有五十年“家门鼎盛”的时期。曾祖辈四名进士,曾祖父吴国对高中探花;祖父辈两名进士,其中一名榜眼。到了吴敬梓父辈,家道开始凋败,吴敬梓亲历了自己家族衰败的过程。
吴敬梓13岁时丧母,23岁时,嗣父又抑郁而死,开始独担门户,因为他在族中的嗣子身份,又是两代单传,便成了族人欺凌的对象,祖遗也被侵夺。他从中看透了封建礼教的虚伪,人情世态的冷暖,从此过着放荡不羁的浪子生活,“千金一笑买醉酣,酒酣耳热每狂叫”,不久“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他怀着誓将去汝的决绝,永远离开故乡,举家移居南京秦淮水亭。
二十九岁,应滁州试(乡试预考),主考官认为他“文章大好人大怪”,不中。1733年,三十三岁时,离开家乡,移居南京。
在南京,因为乐善好施,不懂持家,再加上愤世嫉俗以至于放浪形骸而大肆挥霍钱财,不到10年,就将遗产消耗一空,所以生活越来越窘迫,经常过着衣不保暖、食不果腹的困苦生活,仅靠贩卖文章和朋友的周济为生。
在南京,为了修复南京先贤祠,他捐卖了祖屋,从此生活更加困顿,后来靠典衣卖文度日,到了无物可卖时,只有断炊挨饿。然而性情豪爽的吴敬梓丝毫不以为苦,依然豪放旷达,率直真诚,追慕先贤,淡泊明志,以颜回式的态度笑对人生。平日里他广交文人学士,被四方的“文酒之士”推举为盟主。虽然憎恶灭杀人性的封建礼教,但他还是重视秩序的力量,曾积极地倡导建立先贤祠,试图弘扬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精神以挽救世风。在严冬与朋友五六人,“乘月出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清操,中途退出了博学鸿词征召,以一生“侯门未曳据”而自豪。1751年,乾隆南巡,来到南京,士人夹道拜迎,他却“企脚高卧”。1754年,在贫病交加中客死扬州。
吴敬梓从小“笙簧六艺,渔猎百家”,他曾热衷于科举,中过秀才,但因“文章大好人大怪”而困顿场屋。在南京,他广泛接触了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等社会各阶层人物,认识到科举制度的毒害,从而发出了“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质疑,后来干脆放弃了诸生籍,“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在他35岁那年,江宁训导唐时琳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他却在省试时借病推辞了。
作为一个社会“异类”,科举并未成为吴敬梓对人生的唯一追求,读书生活更使他显露出孤傲脱俗的叛逆个性。当他家业败落后,受到一些衣冠楚楚的士人的冷眼和嘲弄,经历了由富贵到贫贱的不寻常变故的吴敬梓也因此饱尝世态炎凉,体察到士大夫阶层的种种堕落与无耻,看清了封建王朝统治下政治的腐败与社会的污浊,了解了儒生的生活真相和精神状态。从40岁开始,吴敬梓怀着愤世嫉俗的心情,耗费十年功夫写下了著名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后世称其为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奠基之作。不仅如此,饱览诗书的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12卷和《诗说》7卷,无愧为一代文坛宗师。
看鲁迅如何读《儒林外史》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数年挥旧产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乙卯,安徽巡抚赵国麟举以应博学鸿词科,不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乾隆十九年卒于客中,年五十四(1701—1754)。所著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皆不甚传(详见新标点本《儒林外史》卷首)。
吴敬梓著作皆奇数,故《儒林外史》亦一例,为五十五回;其成殆在雍正末,著者方侨居于金陵也。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敬梓又爱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所作传云)故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如令选家马二先生自述制艺之所以可贵云: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
《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详见本书上元金和跋)。此马二先生字纯上,处州人,实即全椒冯粹中,为著者挚友,其言真率,又尚上知春秋汉唐,在“时文士”中实犹属诚笃博通之士,但其议论,则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至于性行,乃亦君子,例如西湖之游,虽全无会心,颇杀风景,而茫茫然大嚼而归,迂儒之本色固在。
至叙范进家本寒微,以乡试中式暴发,旋丁母忧,翼翼尽礼,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两人(张静斋及范进)进来,先是静斋谒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第四回)
此外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其述王玉辉之女既殉夫,玉辉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第四十八回),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详见本书钱玄同序);作者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托稗说以寄慨,殊亦深有会于此矣。以言君子,尚亦有人,杜少卿为作者自况,更有杜慎卿(其兄青然),有虞育德(吴蒙泉),有庄尚志(程绵庄),皆贞士;其盛举则极于祭先贤。迨南京名士渐已销磨,先贤祠亦荒废;而奇人幸未绝于市井,一为“会写字的”,一为“卖火纸筒子的”,一为“开茶馆的”,一为“做裁缝的”。末一尤恬淡,居三山街,曰荆元,能弹琴赋诗,缝纫之暇,往往以此自遣;间亦访其同人。
一日,荆元吃过了饭,思量没事,一径踱到清凉山来。……他有一个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后。这于老者也不读书,也不做生意,……督率着他五个儿子灌园。……这日,荆元步了进来,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时不见老哥来,生意忙的紧?”荆元道,“正是。今日才打发清楚些。特来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壶现成茶,请用一杯。”斟了送过来。荆元接了,坐着吃,道,“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却是那里取来的这样好水?”于老者道,“我们城西不比你们城南,到处井泉都是吃得的。”荆元道,“古人动说‘桃源避世’,我想起来,那里要甚么桃源。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样事也不会做,怎的如老哥会弹一曲琴,也觉得消遣些。近来想是一发弹的好了,可好几时请教一回?”荆元道,“这也容易,老爹不嫌污耳,明日携琴来请教。”说了一会,辞别回来。次日,荆元自己抱了琴,来到园里,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在那里等候。……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边。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自此,他两人常常往来。当下也就别过了。(第五十五回)
然独不乐与士人往还,且知士人亦不屑与友:固非“儒林”中人也。至于此后有无贤人君子得入《儒林外史》,则作者但存疑问而已。
《儒林外史》初惟传钞,后刊木于扬州,已而刻本非一。尝有人排列全书人物,作“幽榜”,谓神宗以水旱偏灾,流民载道,冀“旌沉抑之人才”以祈福利,乃并赐进士及第,并遣礼官就国子监祭之;又割裂作者文集中骈语,襞积之以造诏表(金和跋云),统为一回缀于末:故一本有五十六回。又有人自作四回,事既不伦,语复猥陋,而亦杂入五十六回本中,印行于世:故一本又有六十回。
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鲁迅)
有关《儒林外史》的小故事
(1)周进的故事
周进屡试不第,在山东衰州府汉上县薛家集一所蒙馆教课糊口。新中的年轻秀才梅玖当面嘲笑他,举人王惠轻慢他,荐馆的夏总甲嫌他不常去奉承,村人也嫌他呆头呆脑,他因而连这只“破碗”也端不住了,只能跟着姐夫金有余去买货。一次,偶去省城“贡院”观光,那是专门举行乡试的场所,他触景生情,只觉无限辛酸,委屈得“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众人不忍,凑钱帮他捐了个监生入场应考,不想居然中了,旁人阿谈拍马且不说,他居然自此官运亨通,三年内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他吃足科举之苦,当了权后觉得要细细看卷,不致屈了真才才好。
(2)范进的故事
老童生范进,应考二十余次,总是进不了学。此番应试,适逢周学道主考,出于同病相怜,填了他第一名。范进求官心切,不顾岳父胡屠户的臭骂,继续又去城里参加乡试,谁知中了举人。范进得知中举消息,欣喜若狂,两手一拍,不省人事,被他岳父一记巴掌,方始打得醒过神来。这范进中举以后,有送田地的,有送店房的,有投身为仆以图荫庇的,趋炎附势,不一而足。三两个月光景,家奴、丫鬟都有了,钱、米更不消说,乐极生悲,却把个老母活脱脱喜死,而“七七之期”一过,他便急着和张举人一起奔赴各地去打秋风了。
不容错过的经典
马二先生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楼跟前坐下。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都梳着挑鬓头,也有穿蓝的,也有穿青绿衣裳的,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绸单裙子。也有模样生的好些的,都是一个大团白脸,两个大高颧骨;也有许多疤、麻、疥、癞的。一顿饭时,就来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掮着一把伞,手里拿着一个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庙里去了。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合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倒觉得有些滋味。吃完了出来,看见西湖沿上柳阴下系着两只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一个脱去元色外套,换了一件水田披风;一个脱去天青外套,换了一件玉色绣的八团衣服;一个中年的脱去宝蓝缎衫,换了一件天青缎二色金的绣衫。那些跟从的女客,十几个人也都换了衣裳。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个丫鬟,手持黑纱团香扇替他遮着日头,缓步上岸,那头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远,裙上环佩丁了当当的响。马二先生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
往前走过了六桥,转个弯,便像些村乡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间走了一二里多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厌。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着一走路的,问道:“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那人道:“转过去便是净慈、雷峰,怎么不好顽?”马二先生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见一座楼台盖在水中间,隔着一道板桥,马二先生从桥上走过去,门口也是个茶室,吃了一碗茶。里面的门锁着,马二先生要进去看,管门的问他要了一个钱,开了门放进去。里面是三间大楼,楼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书,马二先生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理一理宝蓝直裰,在靴桶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药板,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拜毕起来,定一定神,照旧在茶桌子上坐下。傍边有个花园,卖茶的人说是布政司房里的人在此请客,不好进去。那厨旁却在外面,那热汤汤时燕窝、海参,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马二先生又羡慕了一番。
出来过了雷峰,远远望见高高下下许多房子,盖着琉璃瓦,曲曲折折无数的朱红栏杆。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一个极高的山门,一个直匾,金字,上写着“敕赐净慈禅寺”。山门傍边一个小门,马二先生走了进去,一个大宽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砖,才进二道山门,两边廊上都是几十层极高的阶级。那些富贵人家的女客,成群逐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都穿的是锦绣衣服,风吹起来,身上的香一阵阵的扑人鼻子。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中,一幅乌黑的脸,捵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后后跑了一交,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上面一个横匾,金书“南屏”两字,——吃了一碗茶。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橘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一饱。马二先生也倦了,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因为走多了路,在下处睡了一天。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E-MAIL:dandanxi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