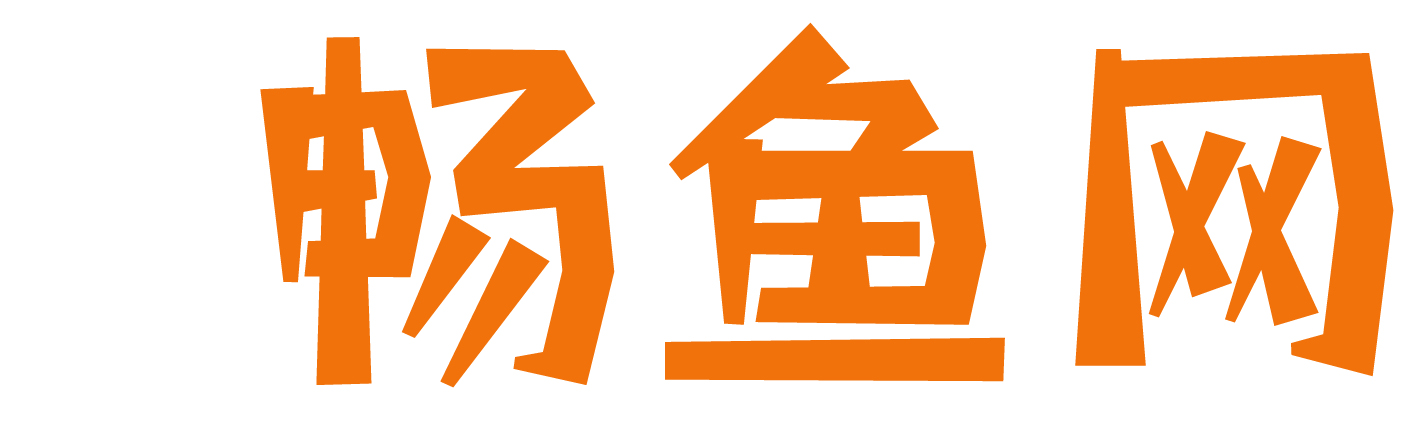安妮·埃尔诺斩获诺奖,是女性写作的一次胜利?| 清醒蹦迪
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都会牵动一些目光。虽然对于许多人来说,几乎不必期待自己钟爱的那些知名作家出现在领奖台上了,但总能“捧火”一些陌生名字的诺奖却也实打实地像一份读书指南,能够拯救书荒的人,充实文学爱好者的待读清单。
今年,这个名字是安妮·埃尔诺。不少媒体声称她“并不冷门”,但随便在购书平台上检索一下,就会发现她的作品被译成中文的并不多,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悠悠岁月》恐怕也没有那么为人熟知。尽管有出版社在紧锣密鼓地推出她三部重要作品,但多少有点“押宝”的性质。可见,安妮·埃尔诺对国内读者来说相对比较陌生的。
并不陌生的是媒体、出版社有意无意给她贴上的标签,比如「描写底层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比如「私人叙事」、「战后作家」,其中最值得琢磨的莫过于「女性写作」。
# 大于“女性写作”的女性写作者

诺奖给埃尔诺撰写的人物小传是“作品主题是身体和性;亲密关系;社会不平等以及通过教育完成阶级蜕变的经历;时间和记忆;以及如何写下这些经历的问题”。
对应埃尔诺的创作历程——《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分别讲述其父亲和母亲的人生故事,将工人阶层家庭生活的历史和社会时代的变迁紧密地结合;《耻辱》写一个“小镇做题家”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跃迁,但也因此失去精神和文化上的阶层归属感的尴尬困境;《女孩的记忆》描述她青少年时期不成功的性经验、对身体的探索;《单纯的激情》(Passion Simple)写她与一名外交官的婚外恋;《正发生》写一个贫困的女大学生因非法堕胎而遭受的不公对待和精神暴力;《我仍在黑暗中》记录她作为女儿对身患阿兹海默症的母亲的凝视……
当一个作家是女性,她的作品又和身体、性或性别密切相关,似乎就很容易被冠以“女性写作”的头衔。更何况埃尔诺的写作的确有强烈的私人叙事色彩,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脱胎于她个人的某段真实经历,其中也不乏对性的直白描写,这种对于个体重要经历近乎强迫式的审视和重新书写也恰好是女性文学的鲜明标记。
随着性别议题不断升温,给女作家贴上“女性写作”的标签好像成了一件趁手且一举两得的传播利器——话题热度有了,受众的理解成本也降低了,还能格外吸引女性读者的关注。但女性写作到底指向什么?身体写作?女性化的私小说?直白露骨的性经验描写?自传式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展演?

《正发生》改编自安妮·埃尔诺的小说,讲述一个女孩因为非法堕胎而经历的磨难,香港译名为《孕辱》,安妮的原著中这样描写女孩得知自己意外怀孕后的心情:”我得了一种只攻击女性的病“。
如果只是这样,那埃尔诺写作价值的衡量维度远远不是这一个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或者说,这个标签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狭隘性)。成长、欲望、情感体验、性经验、代际关系,即便埃尔诺处理的主题都非常“女性向”,我也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她恰巧是一位女性,她处理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处理自己底层出身的工人子女的身份时,所用的“临床医生般敏锐的目光”(诺奖颁奖词)别无二致,并没有为了伸张某种政治诉求而扭曲书写和观察的姿态。
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的故事与我这一代人的故事以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混杂在一起……我书中的事件属于每个人、属于历史和社会学”。纽约客评论家给了安妮·埃尔诺另一种形容:对法国人生活的世俗一面进行犀利审视的“城市意向家”,侧重的也是埃尔诺在用个体经验串联和表征某些特定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一个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和经验的能力。

年轻时的安妮·埃尔诺
更大而化之地说,埃尔诺处理的也不过是文学的基本主题「人的生存问题」:一个出身不高但雄心勃勃的女孩怎样摆脱和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层,怎样忍受这种背叛带来的困顿与痛苦,怎样用“半乡下人半城市人”的视角观察城市和乡村之间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面目。如果你看过韩剧《我的解放日志》,每天在京畿道和首尔之间穿梭,在地铁上默默观察一切的女主角美贞倒是有几分埃尔诺的影子。
埃尔诺曾说:“我开始写作是因为我发现找不到回去(我来的地方)的方式,写作是一种尝试”,对她来说,性别造成的身份焦虑远不如阶层和出身带来的不适感那么明显。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E-MAIL:dandanxi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