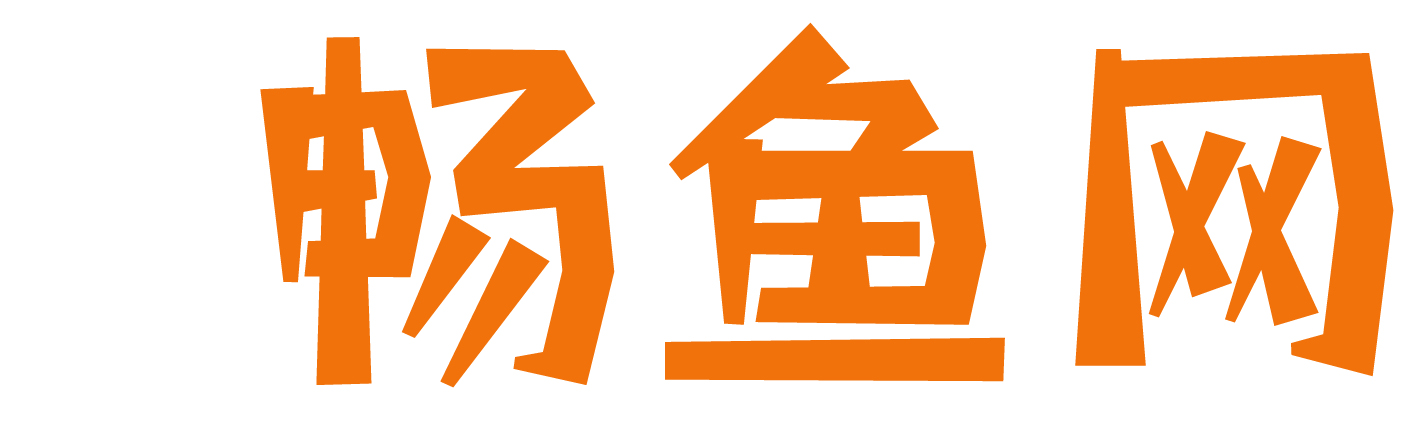杨维恒
作者简介:杨维恒(1986- ),男,山西稷山人,哲学博士,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太原 030006
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17 年 03 期
原发期刊:《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6 年第 20166 期 第 28-33 页
摘要:20世纪40年代,中间代谢和内分泌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拥有着各自不同的实验研究体系和学科语言系统。萨瑟兰作为中间代谢领域的一名研究者,使用内分泌学的学科语言首次提出了“第二信使”的概念。在“第二信使”知识构建的过程中,科学修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暗示修辞就是一切。只有对生化技术的娴熟运用,才使得萨瑟兰得到一个观察。而这个观察作为发现的硬核,通过科学修辞的手法在新的语境下被重新解释,从而最终形成一个新的知识构建。
“第二信使”的出现距今已经经过了51年的时间。这一概念的提出为生物学中细胞信号的转导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在内分泌学中仍然被广泛地运用。然而,这一概念最初却是由一位对激素感兴趣的生化学家——萨瑟兰(Earl A.Sutherland),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出的。在这次会议中,萨瑟兰作为一名中间代谢领域的研究者,没有使用他所在学科的语言,而是使用内分泌学的学科语言,首次提出了cAMP对激素行为发挥“第二信使”(second messenger)的作用。[1]623-626他指出:“简而言之,在激素控制的表达中,自然(nature)总是使用一个‘二信使系统’(two-messenger system)。”[1]623显然,这样的表述具有明显的修辞作用。它使得“第二信使”更像是有待于被发现的自然界客观实体。同样,在一份实验报告中显然通常也不允许像萨瑟兰对“自然”概念这样的使用。也就是说,在一次综述性的会议发言中,萨瑟兰在没有任何理论和实验的依据下,提出了“第二信使”的语义构建。在这个过程中,“第二信使”的语义构建并没有同萨瑟兰之前的实验工作相关联,也没有来自于新的实验数据,而仅仅是使用新的语言对旧的实验数据的一种再语境化表达。正是这种再语境化的表达,使得1956年发现的分子在1964年又变成了新的发现。而这个发现,仅仅在7年之后就被授予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一、“第二信使”的语义跨界——中间代谢与内分泌学:两个不同的研究传统
20世纪40年代初,中间代谢的研究领域就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学科语言。人们约定中间代谢的研究目标就是阐释中间体的本质,并且研究糖、脂肪、蛋白质在新陈代谢中的转化过程。新陈代谢被看作是一套协调的有顺序的酶催化反应。在这个反应中最初的物质经过中间物质被逐渐地转化成最终物质。其中每个转化都需要一种特殊的酶。这些催化反应的序列被称作新陈代谢的路径。合成反应需要能量,分解反应能够释放能量。能量和酶始终是这个学科论述的两个关键词。同一时期,内分泌学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黄金阶段。大量的激素被相继发现。对这些激素生理功能的研究也在不断提高着人们对内分泌的认识。但是,这两个学科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实验研究体系及学科语言系统。就像罗伯特·科勒(Robert Kohler)所指出的那样:对中间代谢的研究是传统的生化学家所关注的领域,他们不受制于要使用动物的吃力技术,然后能够迅速地去阐明生物个体合成路径的各个阶段;而与此相反,内分泌学依然是一个医学和生理学学科,并且内分泌学科所获得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于生化学家。[2]
在器官和细胞间交流的思想一直以来在内分泌学中都占据着支配地位。1905年,斯塔林(Ernest Starling)在克鲁尼安讲座(Croonian Lectures)中提出了“化学信使”(chemical messengers)术语,用来指明与生物体功能相关联的化学物质。之后根据一位语言学家的建议,他将由内分泌腺体分泌的“化学信使”最终命名为“激素”。由于斯塔林的贡献,在20世纪30年代,“化学关联”(Chemical Correlation)的思想已经进入内分泌学。当时内分泌学已经发展成在细胞间和器官间进行“化学交流”(chemical communication)的科学。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信息理论的术语开始渗入内分泌学的语言。
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相比于中间代谢的研究者而言,内分泌学家并没有自己的生化实验系统。他们通过对激素生理功能的研究为生化学家提供新的分析对象。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多数激素的结构就都已被阐明。这样一来,在生化知识和激素生理机能之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激素作用机理的知识人们了解得非常有限。内分泌学家认为激素应该是在细胞和生化的水平上作用于靶器,所以,他们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这些物质代谢的途径在体内如何保持平衡、激素是如何作用的?就在这一时期,一些生化学家开始进入内分泌学寻找新的研究领域。他们希望通过在无细胞的环境下对酶和中间代谢的研究去解决激素的作用机理。二战以后,离心技术和超速离心技术的发展使得生化学家对之前称之为“细胞质”的物质有了更精确的研究。此时,中间代谢的研究者不仅假设化学反应的过程在细胞环境和无细胞环境下是一样的,并且还假设化学反应的发生在实验室与在有生命的生物组织中是相同的,尤其是活细胞的功能能够并且也应该通过有序的生化反应来解释,因此生命能够也应该在试管中得以研究。萨瑟兰便是这一运动的一个引领者。他的目标就是在试管中研究激素的作用。而他特定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为日后“第二信使”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萨瑟兰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了自己的医学博士学位。此时科里夫妇(Carl Ferdinard Cori和Gerty Theresa Cori)以及他们的团队也在那里工作。在这一时期萨瑟兰就跟随科里夫妇工作,但是之后由于二战的原因他到美国的一个医疗队伍中去服役。在诺贝尔奖演说中,他曾说道:我回到了圣路易斯,但是并不能决定应该从事医疗实践还是进入科学研究。科里使我确信科学研究是我前进的正确方向。……科里实验室的学术环境、年轻人“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的存在以及工作在那里有才华的研究者都极有利于这一决定。[3]不难想象,他的医学训练让他比大多数的生化学家拥有更多关于内分泌学的知识。而在著名生化实验室中关于中间代谢领域高度严格的实验训练,也使他拥有的生化实验素养以及使用的技术设备和实验工具都是内分泌学家无法获得的。这也使得日后他能够在两个学科之间随心穿移。
尽管,在科里实验室中萨瑟兰很快就成为中间代谢和酶化学领域的专家,但是他一直以来对激素都很感兴趣。后来他明确表示过:在学生时期,我对激素的行为就很感兴趣,也很感困惑。[4]而作为一名中间代谢领域工作的生化学家,萨瑟兰也遵循着这一领域的学科规范以及学科语言。他认为,激素激活酶,并且在试管中应该能够再现这些作用。这些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说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大约在25年前,我第一次进入激素作用的研究,当时在生物学家之间有个普遍的感受,那就是激素作用不能在无组织的细胞结构中有意义地被研究。然而,我仔细思考了生化的历史,在我看来激素在细胞的水平上作用是真正具有可能性的。[3]
在20世纪30年代末科里夫妇就已经阐明了肝糖原在肝脏中降解和合成的步骤。他们使用肝脏切片已经基本弄清了糖原分解的机理,并因此获得了194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但是,激素促进糖原分解的机制并不清楚。萨瑟兰在科里夫妇研究的基础上,决定继续使用肝脏切片去研究高血糖激素对肝脏的作用。因为,高血糖激素对肝糖原的分解和葡萄糖的产生快速、明显,并且又具有很好的可重复性。在研究的过程中,萨瑟兰采取了一种渐进的策略。他先向内分泌学家证明他研究的两个高血糖因子确实是激素。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1949年的一篇会议论文中,他没有使用中间代谢的学科语言,而是尽量使用内分泌学家的论述去说服他们。他强调两个高血糖因子的行为依赖于完整的细胞组织。与此同时,他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可以使用中间代谢领域研究中被证明是成功的概念和技术来研究激素的作用。[5]441-443在文章最后,他明确地指出:“虽然,在细胞提取物中很多生物物质的中间代谢已经被成功地研究,但是在这些系统中再现激素的生理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文章的目的是讨论高血糖——肝糖原分解因素与肾上腺素对肝糖原分解的作用,强调在中间代谢中关于它们作用的解决方法”[5]441。然而,会议的讨论表明内分泌学家主要感兴趣的是高血糖因子的生理作用以及“真正的激素只作用于完整的细胞,这可能应该是对于激素的标准之一”。萨瑟兰回复道:“我不想暗示激素不能作用于完整的细胞之外。我只是说,除了在完整的细胞中,很难证明其生理意义的效果。我认为,我们应该不断地期待着能够在生命系统之外建立模拟系统来证明这些效果。”[5]462-463
1951年,萨瑟兰最早将激素与酶的活性联系在一起。他证明了在高血糖激素的作用下肝脏磷酸化酶的活性明确而又快速的上升,肝脏磷酸化酶是参与糖原转化成葡萄糖最后一步的酶。对于内分泌学家而言,这已经证明了在完整的细胞结构中激素作用酶的理论。但是对于萨瑟兰而言,他并不满足于此。1956年,萨瑟兰第一次尝试在无细胞系统中研究激素对酶的作用。他将肝脏匀浆离心处理,在得到的上清液中加入激素,此时激素的激活效应消失。但是,他并没有公布这一负面结果。而是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更多的实验研究来解释失败。为什么在无组织的细胞浆液中激素就失去了对酶的激活作用?萨瑟兰猜测,在激素和酶之间还有中间的作用环节,而这个环节很有可能就在细胞膜上。他将高血糖激素与细胞膜在适当的条件下进行反应,然后用高温将高血糖激素与细胞膜上的所有酶都处理掉,再用处理后的成分与酶发生反应,结果酶的活性大大增加。这样就可以得出:高血糖激素并没有直接作用于肝磷酸化酶,而是通过某个既不是激素也不是酶的中间因子。这种未知的、意想不到的分子究竟是什么?萨瑟兰他们也不知道,只是将这个分子命名为“热稳定”(heat-stable)因子。1957年,他们发表了题为“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对肝磷酸化酶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of Epinephrine and Glucagon to Liver Phosphorylase)的论文。现在看来,这篇论文无疑被科学家们认为是一篇关于环腺苷酸(cAMP)的关键性论文。但在当时来看,无论是论文的标题还是内容都无法将其定义为一篇关键性论文。论文标题中并没有提到新分子的发现,内容中作者们也无法对这一发现提供清晰地说明。他们只能证明存在对激素作用看似很重要的新分子。但是并没有找到这个因子。因此,无法使用传统的理论框架去解释这个新的发现。并且,这篇论文标题以及之后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系列的论文标题都属于新陈代谢框架内研究的经典问题。这样也就没有引起内分泌学家的关注。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热稳定因子的结构,萨瑟兰写信请教美国的核苷酸研究权威利昂·赫佩尔(Leon Heppel)。机缘巧合的是,华盛顿大学的李普金(David Lipkin)团队也在研究一个非常相似的分子。李普金也在同一时间向赫佩尔寄了一封关于这一分子的信。而赫佩尔又将他们的信分别交换给了对方。也正是这样的一些沟通促进了新分子结构的确定。热稳定因子被证明是环状核苷酸,最终被命名为cAMP。在之后的两年中,cAMP被证明存在于许多内分泌组织中。这些事实也支持了它在激素作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论断。那么,cAMP和激素作用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萨瑟兰试图建立激素作用机制的统一理论。1960年的一次综述会议上,他尝试通过肝磷酸化酶的活性去解释不同激素的所有作用以及不同激素的降糖作用。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多数科学家的认可。尽管这次的尝试失败了。然而,关于激素作用机制的猜想开始在内分泌学的科学共同体中逐渐流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除了肝脏,在心脏、肌肉以及大脑中都存在cAMP,并且脊椎动物的含肽类激素都可以引起cAMP浓度的升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萨瑟兰在1964年的一次会议发言中出乎意料地介绍了“第二信使”的想法。激素(第一信使)激活ATP转化为cAMP(耐热因子),然后,cAMP作为被称为“第二信使”的角色使有机体产生生理反应。显然,“信使”的隐喻表述帮助他们隐瞒了无法解释cAMP如何作用的事实。[6]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修辞策略使得1956年发现的分子,在1964年又变成了新的发现。
二、“第二信使”构建过程中的科学修辞
萨瑟兰使用内分泌学的语言成功构建了激素作用的表征。而这种修辞性的表征比解释性的意义更具有启发性。它开拓了内分泌学研究的新领域,开启了细胞和分子内分泌学研究的新时代,奠定了细胞信号转导研究的基础,使得细胞间通过信使分子方法相互交流的思想成为一种主导。那么,在“第二信使”科学语言形成的过程中是如何运用科学修辞方法的?这需要对“第二信使”构建过程中的语形修辞、语义修辞以及语用修辞展开具体的分析。
“一般认为,科学研究领域的语言分为三个部分:逻辑语言、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7]111其中,逻辑语言是一种纯粹的符号语言;观察语言是对日常可观察实体的一种语言表达;理论语言是对日常无法观察或测量的实体的语言表达。“第二信使”就属于理论语言,它是不能直接把握的抽象性实体。虽然可以使用不同的途径对其进行鉴定和判断,但是并不能对其进行直接的观察和测量。所以,只能先使用某种语言或符号对其进行表征,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修辞分析。也就是说,“第二信使”的语言构建也必然要经历“实体——理论——理论表达——理论表达修辞”的过程。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修辞方法的运用。
1.“第二信使”构建过程中的语形修辞
正如前文所言,萨瑟兰在1957年发表的论文是关于cAMP发现的关键性论文。但是,无论从论文的标题还是内容上都不能表明已经获得了这个重要的发现。在此之后到1964年之间,他们发表的实验论文也仅仅被作为是中间代谢研究领域中的经典论文,期间从来没有提到过“第二信使”的表征。通过对萨瑟兰及其团队在1950-1964年发表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发现他们获得的经验数据和“第二信使”的概念之间也没有明显的、逻辑的、必然的联系。如果将他们的研究与“第二信使”分开来对待的话,那么,它们有可能很快就会被历史所遗忘。然而,1964年萨瑟兰对“第二信使”科学语言的构建使得cAMP成为新的发现。这是一个全新的语言构建,在之前的任何论文中都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实验或理论的依据。正是这样的语言构建,使得他们的发现成了一个貌似真实的过程。因为,这样的表征能够更好地表达激素作用的机制理论,也能够被科学共同体以及科学受众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换句话说,“第二信使”的构建就“是为了反映或预设最有理由被接受、最没有理由被怀疑的结论”[8]。所以,“第二信使”的语形表征就是使用修辞的手段去重新构建激素作用的理论系统,将细胞信号转导的理论更加具体和形象地揭示与展现出来。
显然,这个过程中“第二信使”的语形表征属于一种模型语言的特点。它将信息理论中“信使”的语义与激素作用过程中“信使”的语义相关联,通过对旧分子的重新定义来表征和解释激素作用的机制。可以看出,从方法论意义的角度讲,“第二信使”的语形修辞为激素作用的机制理论提供了语言系统的表征基础,为细胞信号转导研究的陈述提供了形式化的标准,也为科学共同体对这一理论的接受与抛弃提供了审美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新的”分子被称为“激素作用的第二信使”就引起了各方面更多的关注。就如萨瑟兰在1968年的一本著作中写道:我们使用的语言对我们关于现实的概念有很大的影响,即便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术语,被描述的事物或现象都是一样的。[9]
2.“第二信使”构建过程中的语义修辞
科学修辞的本质并不是通过修辞的手段将科学现象还原为符号或词汇等的语形表征来完成对科学陈述的重建,而是需要通过修辞的手段进一步地在语义的层面创造性地赋予科学语言新的意义。
生物学“信使”的思想源于内分泌学的语言。1905年,斯塔林最初提出了这一思想。但是,在这一时期关于“信使”概念的定义并不精确。直到20世纪40年代,信息理论的术语开始逐渐进入内分泌学的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奥斯卡·海特(OscarHechter)对内分泌学中“信使”概念的精确定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控制论开始成为生物学解释的一个标准。在控制论系统科学中,有机体成为“特定类型的组件”(components of a particular type),生物体是由子系统重新组装拆卸的系统,所有系统都有符号的发送者和接收器。[10]例如,海特在1962年写道:每个活细胞和其周围的液体构成一个单位系统——一个单位生命——展示了生物界的所有基本原则。细胞膜将这个系统分为两个部分——细胞外的环境和细胞内部。正是在细胞膜上,细胞外的各种信息第一次侵犯细胞。正是在这儿,它们被最初接收、评估、然后转发到更深层次的机制去产生需要的行为。在生物学中这是老概念——难怪内分泌学的先驱们相信被称为激素的“化学信使”在细胞表面作用于特定的受体——通过调节底物或者离子进入细胞来影响细胞功能。[11]也就是说,海特使用中间代谢的假说去解释激素作用的研究。他认为更复杂的过程是由激素和所谓是细胞“受体”的结合而发起的,从而“激活”了这个过程,然后能够通过细胞传递环境信息。(受体对激素的)信息回应、(受体的)识别、(关系密切的分子结构之间的)辨别等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控制论语言的术语在他的论述中多次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海特其实利用了两个学科中语言的对应规则建立了它们之间的语义映射、语义替换等,从而实现了“信使”等控制论术语在内分泌学语言中的意义澄清与精确。
“第二信使”的构建同样如此。萨瑟兰尝试将控制论的概念引入激素作用的问题。利用语义之间的对应规则,在“第二信使”不知道以何种方式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就完成了它的语义表达。当然,在这个语义修辞的过程中也实现了“第二信使”假说的经验内容。尽管最初对cAMP作用的观察可能是无意义的,但它确实又是真实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未知的分子参与了激素的作用。
所以,从方法论意义的角度讲,“第二信使”的语义修辞为它的语形表征提供了理由,也使得它的理论假说的经验内容具有了实在的意义。同时,这样的语义修辞也“能够成为词语与对象、理论与实在、抽象与具体、概念与系统相一致的中介,减弱滥用科学语言、歪曲概念指称、修改理论意义的形而上学弊病”[7]112。
3.“第二信使”构建过程中的语用修辞
通过对萨瑟兰论文的分析表明,从新分子的发现到“第二信使”的提出他使用了相当曲折的策略。虽然,他并不赞同当时内分泌学领域学者的观点,但作为内分泌学领域的新来者,通过使用其受众的语言很快获得了内分泌学研究共同体的认可。
1957年新分子被发现之后,萨瑟兰主要的任务便是让科学共同体承认其重要性。这里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是,1957-1958年期间,华盛顿大学的李普金团队也在研究一个十分相似的分子。萨瑟兰和这个团队之间的沟通使得新发现的热稳定因子结构被确定为核苷酸。而在分子生物学发展的初期,由于它的结构与DNA、RAN结构问题的相关性使得它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尽管在当时并没有人会觉得这个新分子有什么重要性。另一方面是,1958年到1960年之间,许多内分泌组织中都发现cAMP的存在。而这一事实支持了它在激素作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论断。因此,接下来的问题便是cAMP与激素作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前所述,萨瑟兰尝试建立激素作用的一般机制,从而去挽救他的理论。尽管失败了,但关于激素作用机制的猜想在内分泌学共同体之间开始流行。
20世纪60年代,信息理论及控制论的术语对于内分泌学共同体而言早已不再陌生。在内分泌学论文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术语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控制论的语言借鉴的。正是在这一时期萨瑟兰在一次会议发言上提出了关于“第二信使”的想法。他不仅使用了“信使”这一术语,还使用了例如“特异性效应细胞”(specific effector cells)、(由内分泌腺体收到的)“刺激”(stimuli)、“调节”(modulator)、“目标系统”(target system)等术语。[1]623-6而这些术语都是属于内分泌学的语义领域。所以,在被内分泌学家所熟悉的新的语义语境下,“第二信使”很容易就被接受了。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修辞构建了“第二信使”的语用语境。在这个语用语境下,萨瑟兰与内分泌学共同体之间以及其他受众之间形成了关于“第二信使”有效的共识界域。而这个界域也决定了人们对“第二信使”的有效理解。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无法解释cAMP具体如何作用的情况下,它可以成为以后研究的一个指导方针。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第二信使”的语用修辞不仅是为其事实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说服方式,更是可以增进人们对其事实的理解,消除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误解,从而成为将修辞者与修辞受众之间相互关联的一种工具。
三、结语
科学文本的形式同它的内容一样都应该受到重视,这一点早已被大家接受。科学文本的形式、结构以及语言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它的内容。萨瑟兰作为一名中间代谢领域工作的生化学家,借助于内分泌学的语言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实现了“第二信使”新的知识构建。显然,跨学科的语言以及综述性的会议发言都可以使得他能够更好地通过修辞的手法,让“第二信使”的知识主张有更宽的语义保留。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科学修辞在“第二信使”构建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修辞就是一切。只有在中间代谢领域严格的生化训练,才能使得他最先得到了一个观察。尽管这个观察在当时是意想不到的以及无意义的,但是它确实是真实的,确实有未知的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激素的作用。当时的情况是,两种不同的实验操作被植入到两个不同的学科语言中时便产生了公认的异常——当在整个活细胞的语境下激素作用的酶理论是被证实的;而在复杂的无细胞语境下这个理论是被拒绝的。此时,萨瑟兰得到的这个观察作为发现的硬核,通过科学修辞的手法在新的语境下被重新解释,从而最终形成了新的知识构建。
参考文献:
[1]SUTHERLAND E W,OYE I,BUTCHER R W.The action of epinephrine and the role of adenylcyclase system in hormone action[C]//PINCUS G.Proceedings of the 1964laurentian hormone conference,volume 21in recent progress in hormone research.New York:Academic Press,1965.
[2]KOHLER R E.From medical chemistry to biochemistry:the making of a biomedical disciplin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325-326.
[3]SUTHERLAND E W.Studies on the mechanism of hormone action[J].Science,1972,177(4047):401.
[4]ROBISON G A,BUTCHER R W,SUTHERLAND E W.Cyclic AMP[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1:1.
[5]SUTHERLAND E W.The effect of the hyperglycemic factor of the pancreas and of epinephrine on glycogenolysis[C]//PINCUS G.Proceedings of the 1950laurentian hormone conference,volume 5in recent progress in hormone research.New York:Academic Press,1950.
[6]BAZERMAN C.Shaping written knowledge:essays in the growth—form func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scientific paper[M].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8:37.
[7]郭贵春.隐喻、解释与科学修辞[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8]MARCELL P,William R S.Persuading science:The act of scientific rhetoric[M].Canton: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1997:98.
[9]SUTHERLAND E W.Cyclic AMP and hormone action[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1:19.
[10]HARAWAY D J.The high cost of information in postwar evolutionary biology[J].The philosophical forum,1981-82,3:252.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E-MAIL:dandanxi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