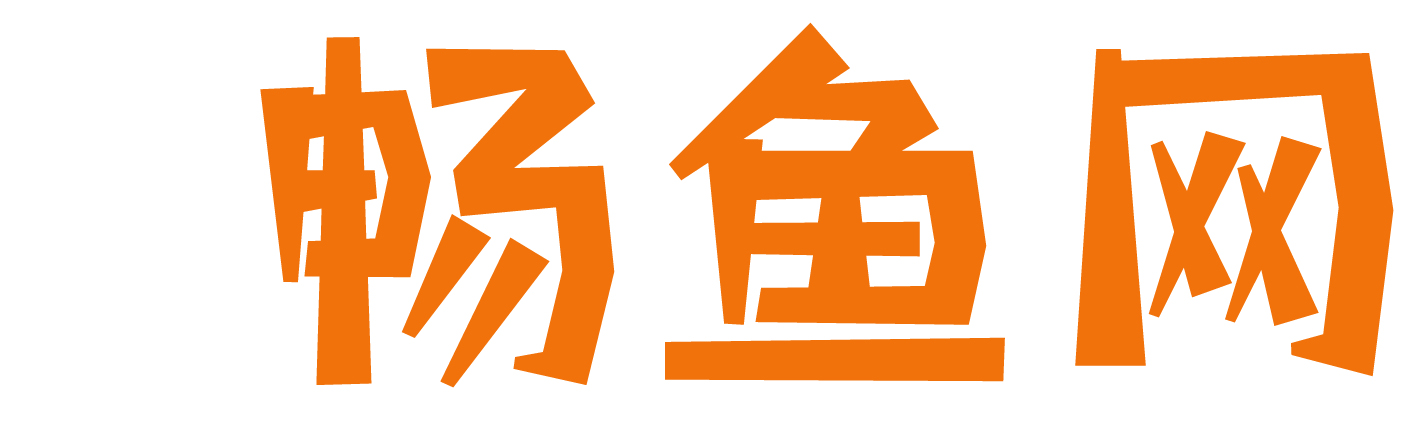顾恺之
顾恺之(约345—406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顾恺之多才多艺,在诗赋书法和绘画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当然最突出的还是他的人物画成就。这一成就使他不仅在魏晋南北朝人物画族群中出类拔萃,鳌头独占,而且对后世也有巨大影响,堪称历代楷模。在这方面,他与书圣王羲之在书法领域中所享有的艺术地位是十分类似的。
考察顾恺之的人物画,大致可以依据如下两种材料:一是作品本身。虽然顾恺之的人物画作品皆为后世之摹本,但这些摹本基本上体现了顾恺之人物画的面貌和水准。另外,南北朝的一些壁画作品亦可作为参证。二是后人对顾恺之及其绘画作品的各种评价以及顾恺之本人所发表的绘画见解,这两种材料相互结合和对照,可以较好地把握顾恺之人物画的真实风貌。
考察顾恺之人物画的语言特征和风格境界,可以首先集中于他的“线条”运用。那么,顾恺之人物画的线条有什么特点呢?从传世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智仁图》及《斫琴图》等作品来看,其线条大都为舒缓、绵劲而细长—这与汉代帛画人物的线条品格是一脉相承的。顾恺之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和创造,使线条显得更加遒劲而富有韧性,更加舒展而从容不迫,更加宛转而趋于精微完善。有学者认为,顾恺之的线条“圆而转”,可能受到当时篆书中锋用笔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从上述作品的线条性状来看,其运笔在控制中,速度比较缓慢,但却毫无滞涩之感,从而呈现出均匀、圆转而又自然的笔调,这与篆书的确是相通的。后来明代詹景风在评价他的《洛神赋图》时说,“其行笔若飞而无一笔怠败”,“亦似游丝而无笔锋顿跌”。还有人用“春云浮空”“流水行地”“春蚕吐丝”等语来形容顾的用笔(线条),可谓形象而贴切。特别是“春蚕吐丝”四字,将顾恺之用笔(线条)之“绵”“缓”“韧”“细“圆”“转”的特点很好地揭示出来了。

东晋·顾恺之
洛神赋图(宋摹本)(局部)
绢本设色
纵27.1 厘米
横572.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顾恺之人物画用笔及风格特点集中地体现在《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中。《洛神赋图》有唐人和宋人两种摹本。我认为唐人的摹本应该更接近顾恺之的画风。作品中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衣纹飘带、面容手足乃至山石树木和云水,完全是以细劲、绵长的线条勾勒而成的。《女史箴图》中的人物描绘,线条更加细健、圆转而飘逸。顾恺之的人物画以“神”取胜,对此后世有不少论述。如唐代张怀瓘说,“象人之美”“顾得其神”。还说:“神妙无方,以顾为最。”大诗人杜甫则赋诗曰:“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张彦远在评价顾恺之所绘的“维摩诘像”时,说他能成功地表现出“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明代何良俊在评价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时说,“此神而不失其自然”“皆有生气”。顾恺之自己也反复强调要“以形写神”,要“传神写照”。很显然,要做到“传神”,首先须着眼于人物仪容风貌的刻画。顾恺之之所以能够以“神”取胜,应该和他人物画的用笔(线条)特点有很大的关系。对此,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有一段相关论述,值得仔细地研读:
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历代名画记·论顾陆张吴用笔》)

洛神赋图(局部)
所谓“紧劲联绵”,就是前文所说的“春蚕吐丝”。这种用笔特点除了表现为“绵”“韧”“细”“圆”“转”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征状,这就是“缓”。然而这里的“缓”之义与张彦远所说的“风趋电疾”却是相牴牾的,如何解释这种牴牾关系呢?应当说,就顾恺之的运笔速度而言,可能是“缓”(慢)的,犹如春蚕吐丝,徐徐而出,否则就不会做到谢赫所说的“笔无妄下”“格体精微”。纵观顾恺之《洛神赋图》等一系列作品,不难发现,他那种从容不迫、绵紧而韧劲的笔调显然是“疾”笔无法做到的,可以想见画家在用笔(线条)进行人物造型时一定是“意存笔先”且“运思精深”的。但就线条本身的性状—或者说,就用笔而产生的视觉感受而言,则不一定是“缓”,而完全可以形成一种“风趋电疾”的审美效果。在这一点上,顾恺之的线条既不同于两汉的帛画—其运笔缓,且视觉效果也缓。也不同于两汉的一些壁画和漆画一味的奔放快疾。毋宁说,顾恺之人物画的用笔(线条)乃是“缓”与“疾”的对立统一。 也就是说,顾恺之的线条既有“绵”“韧”“圆”“缓”的一面,又有“细”“紧”“转”“疾”的一面;它是“春蚕吐丝”“春云浮空”的,又是“流水行地”“风趋电疾”的。前者偏于“静”,后者偏于“动”,是“静”(缓)与“动”(疾)的对立统一。而当线条之运行与人物那种飘逸的身姿、飞舞的裙带融为一体时,其“缓”(静)的一面仿佛隐而不觉了,而“疾”(动)则以非常强烈的趋势和倾向展现出来了,这就是张彦远所说的“循环超忽,调格逸易”。用笔做到这点,人物情态当然会越发见出风采和神气。这都表明,人物画的神气不仅见于眉目容貌的描绘,而且也在于笔墨运用中所焕发而出的风力格调—它托举着人物的造型并循环、弥散在四周。所以张彦远说:“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概言之,线条的美感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姿态和服饰,在表现人物之“神”上都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宗白华曾指出:中国人物画“在衣褶的飘洒的流动中,以各式线纹的描法表现各种性格与生命姿态”。顾恺之将此称之为“助神”,他说,“服章与众物既甚奇,作女子尤丽衣髻,俯仰中,一点一画皆相与成其艳姿”,“作人物骨成而制衣服幔之,亦以助醉神耳”。应该说,服饰(“服章”“衣髻”)有“助神”之功,而描绘服饰的线条(“一点一画”)也有“助神”之能。反之,如果画家在审美创造中忽视线条的作用,忽视线条在人物造型(“形骨”、“艳姿”)中特殊的辅助作用,那么人物之“神”的表现将是很不充分的,按照张彦远的话来讲,就无法做到“全神气”。

洛神赋图(局部)
与此相关的乃是顾恺之人物画造型的“疏体”和“密体”问题。所谓疏、密二体,就是指人物画造型中线条构成的疏密程度。继顾恺之之后,陆探微的人物画就是一种“密体”;而张僧繇以及唐代的吴道子则表现为一种“疏体”。张彦远曾指出:“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他还将顾、陆二人并称为“笔迹周密”之“密体”代表,而将张、吴的“离披点画,时见缺落”划为“疏体”范畴。其实,陆探微(“密体”)和张僧繇(“疏体”)都是从顾恺之那里变化、发展而来的。因而如果顾恺之纯乎“密体”或纯乎“疏体”,那么陆、张两人的“疏密”之体必有一者难以溯源。我认为,顾恺之的人物画的语言构造虽以“密体”为主,但同时还包含了“疏体”因素,是疏密二体兼而有之。例如他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就明显是“密体”,其线条如春蚕吐丝,连绵不已,与“疏体”那种“离披点画,时见缺落”的样式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密体”的形成乃缘于卫协的影响,卫协之“精”在顾恺之的手中发展为更加完善的“精密”。与此相对照,顾恺之《列女仁智图》中的有些人物造型则倾向于“疏体”,其“线条”构造也不像上述两幅作品那样细密连绵,而是呈现出刚健、疏朗之像。这与卫协那种“不该备形似”、以“壮气”见著的画风可能也有一种渊源关系。所以后来的理论家和艺术家对顾恺之人物画有两种评价。如谢赫说顾恺之的绘画“格体精微”,明代詹景风说顾恺之的绘画“精古而雅秀”,“妇人衣饰金装极精丽,使人目骇心惊”。这些评价表明“密体”乃是顾恺之人物画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特征。但还有另一种评价。如宋代黄伯思评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说“此图简古”;“略其玄黄,取其驵雋,惟真赏者独知之”。元代汤垕评顾恺之人物画时说:“初见甚平易,且形似时有或失,细视之,六法兼备,有不可以语言文字形容者。”这些评语乃是对其“疏体”特征的很好说明。后来明代詹景风在指出顾恺之人物画“精古而雅秀”的同时,又说其“俊爽而雅劲”,并认为两者“不妨并传也”。可见顾恺之人物画确有两种(“疏密”)体系。如果联系到他“用笔”上的特点来看,其缓笔则往往为“密体”,为“格体精微”;而“疾”笔则可能倾向于“疏体”,倾向于“简古平易”和“俊爽而雅劲”。

东晋·顾恺之
女史箴图(唐摹本)(局部)
绢本 设色
纵24.8 厘米
横348.2 厘米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上述所阐发的用笔(线条)特点以及“疏”“密”二体构成了顾恺之人物画“语言”的基本样式。但是必须看到,任何语言样式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是隶属于、服务于人物造型(形象)的,而且只有统一于人物的造型,它才会获得审美价值和意义。顾恺之人物画的语言和造型正是这样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顾恺之人物画所特有的风格面貌—高古。
对于这种高古的风格面貌,后世不少理论家和艺术家都有论述。唐代张彦远将顾恺之的绘画(“顾陆之迹”)视为可与“上古”并齐的“中古”风格。其“中古”一词虽然是一个时间概念,但所谓“中古质妍相尽”,则指出了它的风格内涵,表明顾恺之的人物画在内容(质)和形式(妍)上达到了和谐完满的统一,“高古”的气象正是从这种统一中焕发出来的。明代詹景风说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高古神奇”“精古而拙”“意致潇洒”。清代李葆洵说顾恺之的人物画“古朴浑论”,有“古拙之趣”。清代吴升说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此图画既高古。”清代安岐也说《女史箴图》“笔法位置,高古之极”、“洵非唐人所能及也”。可见,“高古”乃是顾恺之人物画风格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顾恺之人物画“高古”风格的形成首先得之于他的线条(用笔)特点。他那绵韧、细劲、若游丝一般的线条所构成的密体,荡漾着一种春云浮空、令人忘尘的“高古”格调和气象。顾恺之的人物画在着色上虽然浓艳,但整个调子仍然纯粹而统一,仿佛是从人物造型以及线条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色相,而不是某种外在的藻饰。明代詹景风说顾恺之的绘画“着色虽浓艳而清澈于骨”。元代汤垕、夏文彦等人也说顾恺之“傅染人物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藻饰”,“不求晕饰”。这表明,顾恺之人物画的着色同样展现了清澈自然的“高古”境界。

女史箴图(局部)
从造型上来看,其人物的绰姿意态之间也流露出一种“高古”的风范。清代叶德辉说顾恺之的人物画“犹存汉石室石阙画像遗意”。李葆洵也这样称赞顾恺之,“虎头妙笔绝古今”,“古朴浑论,类汉画石”。的确,顾恺之人物画在造型上明显带有汉代画像石(砖)那种圆浑质朴的遗风。如《列女仁智图》,人物衣袖宽袍的处理是那样饱满充盈,呈现出汉代画像石(砖)人物画常见的圆弧形的张力与浑朴。《洛神赋图》右边尾端那一组人物的面容描绘,也与汉代画像石(砖)那种椭圆造型相当接近。当然,顾恺之的人物画造型并不是汉代画像石(砖)的简单翻版,事实上,画像石(砖)那种厚重的造型质感在顾恺之这里已为其飘逸的形态所取代。有些作品(如《女史箴图》)的人物造型和姿势更富微妙变化,并呈现出一种清瘦修美的面貌,初现后来“秀骨清像”之倪端。但从总体上看,顾恺之的人物画与汉代画像石(砖)在造型结构上多有契合贯通,经过顾恺之重新锤炼和创造,终于形成了一种“高古”的风格范式。这种风格范式对后世人物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前面谈到,顾恺之人物画十分强调“传神”。他认为,眼睛的刻画对于“传神”具有关键作用(“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此外他还有一个重要见解,即认为人物环境的描写对于“传神”也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顾恺之说:
凡生人无有手揖眼视,而前无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和乖,传神之趣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论画》)

东晋·顾恺之
列女智仁图( 宋摹本)(局部)
绢本 设色
纵25.8 厘米
横470.3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这就是讲,画家所描绘的人物,不能脱离一定的环境(“所对者”),否则就不可能达到“传神”的目的,即所谓“空其实对”,“传神之趣失矣”。而且不仅不能“前无所对”,同时也不能“对而不正”—画家必须在审美创造中注意到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微妙的呼应关系,这就叫做“悟对通神”。顾恺之这些见解十分精彩,这是绘画实践的深刻总结。他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都是“悟对通神”的典范之作,如《女史箴图》中的汉武帝与班婕两人关系的描绘就是如此。图中班婕端庄伫立,汉武帝则在车辇中回首相招,这不仅很好地表现了“班婕有辞,割欢同辇”的情节,而且将汉武帝和班婕各自的心理状态(“神”)在这种难舍难分而又坚辞同辇的关系中非常生动地揭示出来了。该图卷尾的两位偕行的女子,体态绰约,相顾而语,眉目之间,神气相融。《列女仁智图》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两两相对,或俯或仰,或正或侧,或招呼或回应,其卫灵公与灵公夫人“悟对通神”的情状更是意韵连绵,缱绻不已。
以上所说的环境(“所对者”)乃是指人际关系。此外,顾恺之的人物画还十分注重自然环境的描写,这同样关系到人物之“神”的传达和表现。如画名士谢琨,置于“丘壑”之中,这样才能将他那超凡脱俗、寄情山水的人生情态(“神”)完整地展示出来,而《洛神赋图》更是这样一幅代表作品。图中人物“披罗衣之璀粲”,“曳雾绡之轻裙”,柔情绰态,转盼流精。随着长卷徐徐展开,布列如织的山峦、佳木、流水等自然景物如汉画中的祥瑞一样笼罩着每个人物,从而使画面洋溢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而迷离的氛围,人物神气则在这种氛围中悠然恍惚地弥漫开来—此乃顾恺之在对人物与自然环境描绘中所营造出来的意境之美。正如唐代张怀瓘在评顾恺之绘画时所说:“虽寄迹翰,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洛神赋图》的构图也颇具匠心,人物安排错落有致,时前时后,忽聚忽散,既有节奏感,又有秩序感。自然物象与人物相互穿插而又浑然一体,图中所描绘的远山、远水及上空的飞禽与近景若即若离地拉开了层次和距离,从而使人们在视觉上产生了一种纵深感。画面的中后部分,视野逐渐疏旷开朗,境界变得杳渺而空阔,主人公对洛神的眷恋不舍、惆怅无着之情仿佛随着空阔的境界而显得茫茫无垠而遥不可及。“忽不悟其所舍,怅神霄而蔽光”,“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应该说,顾恺之以其视觉语言极为出色地诠释了《洛神赋》所蕴含的浓郁的诗意。
顾恺之在人物画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成就和影响是当时许多画家—无论是顾恺之之前的曹不兴、卫协、荀勖,还是顾恺之之后的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和杨子华,都难以与之争雄。所以唐代李嗣真说“顾生天才杰出,独立亡偶”,“思侔造化,得妙物于神会,足使陆生失步,荀侯绝倒”。很显然,顾恺之的出现,为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昭示了更加明确的审美方向,中国人物画的审美品格在顾恺之手中变得更加清晰起来,达到真正成熟和完善的水准。顾恺之是魏晋南北朝人物画族群簇拥出来的最璀璨的巨星,他的绘画成就是经先秦、秦汉长期艺术历史培植而成的艺术奇葩,他从绘画实践中提取和总结出来的美学观点,与谢赫“六法”一样,堪称千古精论,影响深远。
图文源自网络仅供学习交流如涉版权问题请联系处理!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E-MAIL:dandanxi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