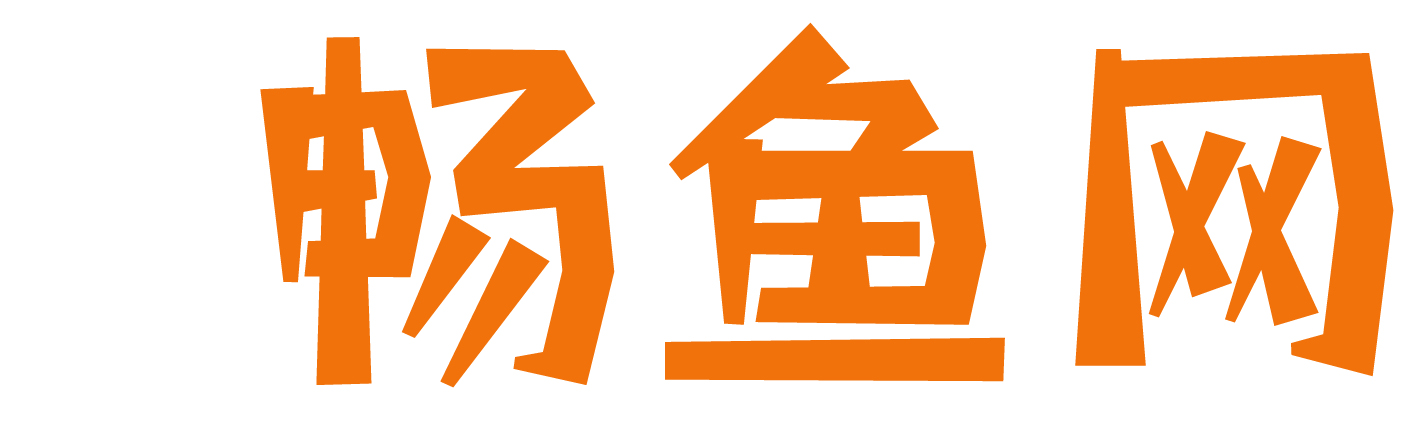生态走马 张洪刚 摄
葛仙米,稻田里的绿精灵
我的老家在鹤峰江坪河河畔一个小小的山村。
江坪河是溇水的一段,溇水是澧水的上游。澧水浩浩,九曲十八弯,最后归于洞庭湖。
江坪河两岸高山负势竞上,与蓝天白云相接。河水从山谷里斗折蛇行,旖旎而去。山麓河岸边,三五成群、依山而建的,是被风雨浸蚀多年木质泛白裂口的吊脚楼。我就在这吊脚楼里、江坪河边出生,慢慢长大。
日复一日是山里人家生活的简单重复,他们从黎明开始计时。
乡村有其独特的迎接黎明到来的方式:雄鸡报晓的声音高亢而清亮;老黄牯仰头长哞厚重而雄浑。四五月间,鸟儿叫得更欢,布谷鸟催农事,水呱呱(一种山鸟)的聒噪在林间树梢更是不绝于耳。声音送走了晨星残月,抖落了几滴叶尖清凉的水露。
几户人家聚居的小村落往往有着相同的家庭结构、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和劳作习惯。他们相互照顾却又暗中较劲,比家庭的殷实,比后人的出息,还比谁家起得早。
天刚亮,几乎每家门口的菜园里,都开始有了弯曲忙碌的身影。瓜菜长得好与坏,全在主人家的手里头、锄头下。山里人把这叫作打早(干早活)。老祖宗传下话,“瓜菜半年粮。”“菜园子是块宝,一年饿不倒。”在艰苦的岁月里,村民靠菜园子弥补了粮仓的不足,填满了一年漫长的日子和人们干瘪的肚子。
鹤峰的山村,大多地处高山险阻,深谷幽涧,出入不便。祖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没有出过山门,居住地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他们在关上了山门的同时,又给村民们打开了一扇天窗。
在那样艰苦,村民还为吃饭犯愁的年代里,稻田里居然生长出一种没有根、没有叶的东西,颗粒饱满、外着胶质、绿中带黑,状如木耳。灾荒之年,祖辈们就尝试着采以为食,救人生命。大家不知此物从何而来,便有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传说。
据说民间叫它“雷公屎”。原因是因为每年春夏之交,它伴雷雨而生,一堆堆的,黑绿黑绿,像蝌蚪,百姓认为是雷公到人间后,雷电交加,用力过猛,屎拉在了田里。老百姓敬神,迷信神,认为神仙拉的屎都是宝,是上天恩赐给饥肠辘辘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圣物。
父亲在母亲起床后不久,就赶紧披衣起床,点一支旱烟,看下老黄牯,拍两下它的头,就开始挽裤脚,找竹筐竹瓢,准备下田去捞“雷公屎”。
太阳从山顶洒出几缕阳光到山谷的时候,父亲的大竹筐也就差不多捞满了。
“雷公屎”捞得多,然后晒干存好,刚好把新米出来之前粮食青黄不接的日子接济一下。长期食用,大家发现这“雷公屎”不仅不臭,还有一丝清香,吃了还体壮身强,这让父母亲多了一身劳动的力量,也让我们儿时的脸庞少了一些饥饿带来的瘦黄。
后来上学了,才知道有史书记载,早在一千多年前,有个叫葛洪的老道人隐居在此,吃“雷公屎”救了饥饿的自己,出山后还送给朝廷,救了体弱多病的皇子。皇帝于是赐其美名,叫“葛仙米”。葛仙米因此每年朝贡,成为宫廷美食。村民不大习惯,依然喊着它的一些土名字:天仙米、天仙菜、水木耳,就像给邻家的孩子叫地婆、妹娃儿、石头这些小名一样顺口顺耳。
既然皇帝老儿都爱吃,能干的家庭主妇自然会不断摸索尝试,做出独特的味道,滋养一家,招待稀客。
大片的稻田前面,是蜿蜒的江坪河,河水是沿途山上无数条山涧溪水汇聚而成。清晨的河道上,薄雾笼罩,淡如轻纱,隔好远,就能隐约听见河水流淌撞击河床的声音。
一条清澈的河流,灌溉着两岸的农田,滋养着两岸的村民,这里有着原始的宁静。
但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个消息,仿佛一枚炸弹,在江坪河两岸的村子里炸开。
据说这里要修建一个大水电站,满足整个鹤峰县供电的需求,造福一方。到时大坝高筑,水深几百米。江坪河两岸的村民都要移民搬迁,离开这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
怨气怒气眷恋茫然,各种情绪弥漫在江坪河两岸,融进哗哗流淌的河里,水声里多了一种幽怨和躁动。
搞科学的、搞测量的、当干部的,拄着手杖,擦着汗水,翻山越岭,一路跋涉,来到了江坪河。那几年来了一拨又一拨,看样子肯定要筑坝了,我们就要搬家了。
时间就在这些人来人往的陌生人忙碌穿梭的身影中,和江坪河的水一样流逝而去。
镇上和村里的干部也开始一拨拨到村入户贴公告,做宣传,要老百姓为全县做贡献,服从大局,迁到更好的地方,建设更美的家园。
几年过去了,房屋、生产工具、牲畜陆续迁走。因为交通不便,人力不够,一些人家的坟茔,那些长眠在河坎上、山坡边、茶园里、树丛间的亲人,就在人们的嚎啕大哭之后,永远地留在了山下。
坝筑起了,水蓄满了,他们就在这青山绿水之下,替子孙永远看守这块他们祖祖辈辈的精神家园。
泪水是最难渡的河流。村民们坚韧地跨过河流,穿越高山,走向新的家园。
多年后,几经挫折,大坝就像乡里干部宣传的蓝图,江坪河被拦腰挡住,变成了库区,成了高峡平湖,江坪河电站发出的电经过一码一码的高压线输送到城市乡村。库区人对祖辈生活之地的眷恋和背离,换来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辉煌。
鹤峰地广人稀,地质结构差不多。新迁的家园依然有青山,有绿水,勤劳的双手依然能建起拔地而起的吊脚楼,房后的山坡上开辟了茶园,房前的开阔地上开垦了稻田。山间清澈的溪水持续不断地流进纵横交错的稻田,四五月间,我们依然可以捞鹤峰人最富有的“雷公屎”。
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政府开始如约修建村民们梦寐以求的环库区公路。
路通了,思想也通了,沿着库区的盘山公路,很多成年村民走出了大山,到大城市打工挣钱去了。
村民们通过孩子了解了山外的世界,了解了很多科普知识,学会了使用网络。
前两年,扶贫干部驻进了村里。因为有了电视、手机和网络,我对国家政策了解一些,知道他们是带着党的政策,带着总书记精准扶贫的任务要求驻村的。
我们开始重视“雷公屎”。不过现在我习惯叫它葛仙米了。因为政府已经把它作为特色农产品推向山外。这个我们祖祖辈辈充饥救命的食物,已然成了当今食材界的大熊猫,价格贵如黄金。
我开始兴趣盎然地听扶贫干部讲葛仙米的食用价值、经济价值,还有药用价值,有空了就抱着手机,女儿教会了我查资料,在网上了解葛仙米。
原来鹤峰人早就发现葛仙米是个宝,很多人都在念葛仙米的致富经了。如果没有网络,我还固执地认为大家都还在守穷。
现在的葛仙米已不再是救命粮,而是洒满稻田的黄金。它没有根须、没有种子,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祖辈给我们留下的美食、药材,它是我们儿时的回忆,是江坪河风吹两岸的稻香和乡愁。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葛仙米越发展越多,名气越来越大,村民的腰包开始鼓起来了,几百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扬眉吐气,甩掉了戴在头上多年的贫困帽子。
村民富了,库区公路改造升级了,政府扶持,把吊脚楼逐渐改造成了青瓦白墙花格窗的新民居,形式结构上依然融入了吊脚楼的元素。致富奔小康的喜悦挂在了村民的嘴角眼角眉梢,挂在了新民居屋檐下的灯笼上。
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扶贫干部回去了,他们创造了奇迹,完成了历史的重任。
傍晚,丫头学校放假回到家。孩子她妈炖了腊蹄子,扯了几把孩子爱吃的鸭脚板(山沟边长的野菜)下汤吃,还特地用葛仙米蒸了一碗鸡蛋羹。吃到葛仙米,姑娘问今年卖了多少钱,在哪卖的。
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卖了十来万,明年还要发展有机稻,双管齐下,田里不闲,手里不空,力争突破二十万。
“老爸,农产品多,农产品好,销售也要有技巧,您知道网上销售吗,吃完饭了,我教您弄。”
吃完饭,父女俩坐在场院里,我当起了闺女的学生。看着姑娘精明能干的巧手拨弄着手机,我暗自感谢,仿佛看到葛仙米从网上源源不断地流出大山,看到大把的钞票从微信里转进来。
那田间墨绿墨绿,晶莹剔透,状如谷粒的精灵,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
好一个绿色的精灵。
深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驻村扶贫干部又来了,他们说中央有新政策出台了,老百姓光脱贫还不行,我们还要振兴乡村,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那时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在梦里,我们都是吃葛仙米长大的“葛仙”。
审核|周志宏
签发|覃佐松
“恩施日报·知恩”客户端▼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E-MAIL:dandanxi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