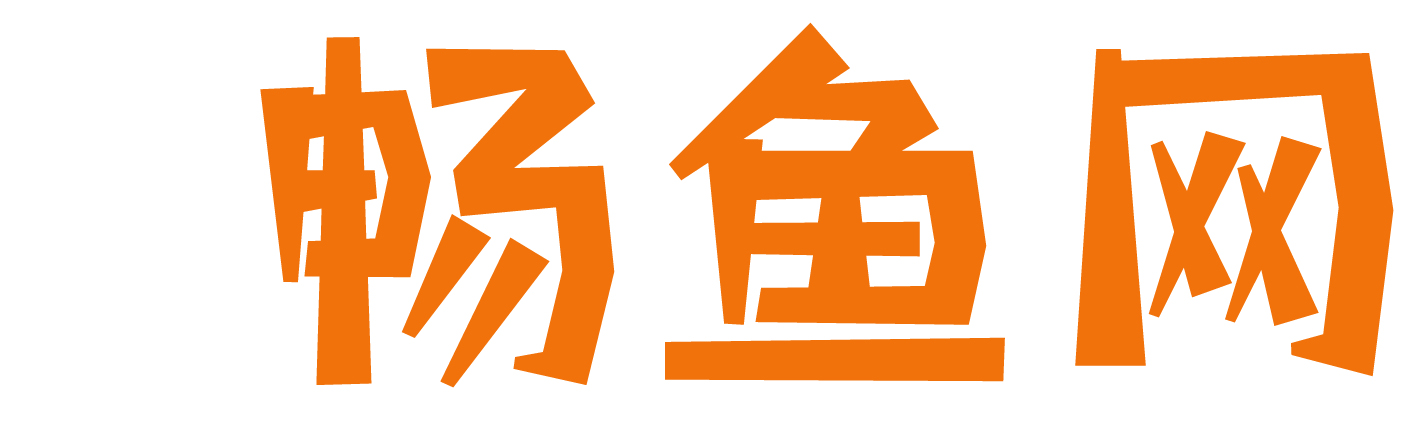杂咸是潮汕人的说法,我以为归纳得很精准,便用在这篇文章里了。宁波不像潮汕人那样每日吃粥;每逢吃粥,若不是一时兴起或是特意培养出的习惯,那必定是在病里或是胃痛。因此宁波人对佐餐的冷盘小菜没有统一的称呼。
宁波人吃得多的是泡饭。泡饭泡饭,白水泡剩饭也。过夜饭用开水泡开,最好是回锅滚一分钟,配一点羊尾笋或蟹糊,可作一餐,甚美。这和粥绝对不同,水米分离,一清二白。这样的一餐吃得舒服,我心目中的comfort food(能让人有宽慰之感的食品),泡饭配杂咸是当之无愧的。我母亲常对蒋介石爱吃泡饭配杂咸作早餐这趣闻津津乐道,认为从中可窥其性格平直节俭。蒋介石是宁波人,但这一趣闻,我身边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宁波杂咸可归作海产、笋子、雪菜三类。大多只用盐,凉拌或快炒一下,少滴一点麻油,吃的是食物的本味。汪曾祺先生专为咸菜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苏州春不老,“寸把长的缨子还是碧绿的,极甜脆”,这样的精致温婉,宁波的杂咸是绝没有的。同为江浙一带城市,宁波就比苏州多出几分冷静、实际的气质,连下饭的咸菜都不例外,大概与自古下海经商,充满冒险精神的文化有关,吃食讲究的是新鲜快捷。
素物中最多的是羊尾笋和雪菜。羊尾笋以奉化县产的最好。买回的盐腌羊尾笋干,用清水浸泡,去除多余的盐分,再用手撕成丝,淋少许麻油,装盘,即成。外婆习惯将笋丝剪成寸把长,这样更容易下口。羊尾笋和冬瓜煮汤,和毛豆子相炒,都是宁波常见的家常菜。腌笃鲜里有时出现的咸笋是不是羊尾笋,我分辨不出来,但我想若用羊尾笋干做,定然不会差。
雪菜由雪里蕻腌制成,味道咸而爽脆,略带酸味。它自身也可下泡饭,但一与肉丝或毛豆子共炒,滋味就提升许多。雪菜和黄鱼一同下汤是招牌宁波菜“上汤雪菜黄鱼”。我外婆做这道菜极好,外面很多饭店卖的,雪菜量不足,鱼汤欠厚又少盐,没有宁波菜气质。鄞州区有一个雪菜博物馆,路过几次,母亲笑道:“现在真是什么博物馆都有,真不知有没有人去看”,足见宁波人将雪菜视作生活中理所应当的一部分。
宁波杂咸中占大头的是海产。宁波地处浙江东北部,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出产各种“透骨新鲜”的小海产,譬如海瓜子,螃蟹之类。宁波人不像有些地方的人,痴迷于几十斤重的大鱼,似乎越庞大味道就越美。我自以为那是不常吃海鲜的人才有的偏见。宁波人很明白,很享受小海鲜独特的滋味。宁波一五星级酒店西餐总厨对宁波海产评价道:“…这里物产丰富,可是宁波人缺少对这些食材的赏识,处理方法粗糙,大多是腌或蒸,我觉得可惜。”这就是外国人对烹饪方法的偏见了,要知道简单处理恰恰代表着对食材原味的尊重。
海产杂咸中最有宁波特色的,我以为是淡菜。淡菜,即青口贝,配薯条乃是比利时国菜。北方人叫这玩意儿“海虹”,这是个在我看来颇浪漫的叫法。煮海虹,似乎把海上雨后的绚烂魔幻都浓缩到锅里了。淡菜味道极鲜,只消处理干净,加一点盐和酒煮熟至外壳打开即可。肉色金黄,汤汁奶白,贝壳青黑,很好看。宁波人煮淡菜,不加别的调料;味精更是万万不可,它只会破坏其鲜味之平衡。淡菜配泡饭,乃宁波一绝;就算是空口吃,一人也可以干掉一大碗。质量好的淡菜才配得起盐水烹煮,这好比新鲜的小黄鱼往往清蒸,质量次之或不新鲜的才会红烧,用浓油赤酱掩盖其缺陷。全国最优质的淡菜出自宁波和青岛。听说上海餐厅大部分的淡菜从宁波进口。
西式的煮青口要复杂得多,要加洋葱,芫荽,辣椒,黄油等,入白葡萄酒闷制至青口壳打开,全程不加一滴水,只靠热力活活逼出汤汁。我估摸这样的成品是配意面吃的。这也只是美食杂志上的描述罢了,我没做过,但可以料想那是一种浓郁的美味。《舌尖上的中国》里提到宁波象山的老人和台湾的兄弟因政治原因久未谋面,终于有机会前往台湾时,带去了一袋干贻贝,以表思乡之情。贻贝和淡菜是同一种东西,但将其晒成干的吃法,我还真没有领教过。新鲜的淡菜,滋味远比干货好。象山人吃海鲜勤,二者的差别定是了然于心,相信干贻贝只是应剧情需要出现罢了。
有一些杂咸是我从来不吃,但常常在餐桌上见到,听到宁波人对其称赞的。比如蟹糊,比如泥螺。蟹糊,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膏炝蟹。取活蟹,去盖去腮,挑出红膏,改刀成小块,再和红膏一起压碎成糊,加盐、糖、酒,即成。这又是一道对原材料质量要求很高的杂咸。吃时蘸醋,下泡饭,宁波人称之“压饭榔头”。泥螺就没什么意思了,只是一种生长在滩涂,包裹着透明硬壳的软体动物。我们家都是买现成罐装的,如“陆龙兄弟”。我对这些生的,黏糊糊的食物有些心理障碍,不知是不是小时候吃了生的海鲜,得病过;每当一大家子一起吃饭,谁是老宁波便彰显无遗——吃蟹糊,泥螺最欢的,莫过我的外公外婆。母亲曾说我简直不像宁波人,“不会说宁波话,不吃海鲜”。我自觉得冤枉。我还是爱吃些花蛤,淡菜,黄鱼的。还有海蜒。海蜒是一种寸把长,两毫米左右宽的小鱼,论斤买,装在塑料袋里,一袋里有小鱼万万条。海蜒加大蒜末同拌,少滴酱油,是很能下泡饭的美味。它似乎也是生的,但我不觉得反感。
我暂时能想到的日常杂咸就是这些。咸蛋、榨菜、豆腐乳等行销全国的杂咸我没少吃,但在这里就不谈了,也实在因为他们不源自宁波。总的来说,宁波杂咸清清爽爽,放的什么料,用的什么工艺,一目了然。从前我认为宁波这城市和宁波菜“简单”——这是礼貌的说法,若不客气起来,就是“没有内涵”。王安石做过明州(即古代宁波)县令,也没见他为红膏炝蟹作一首诗。可现在我以为,这样的简单明了未免不是一种气质。宁波人也实在是把研究吃的精力花到更“现实”的事物上了。
我写这篇文章,一是给在他乡的宁波人看的,为的是挑逗其思乡之情(哈哈),二是给和宁波非亲非故的外地人看。若是为本地宁波人而写,那就真成了鲁迅请密斯高吃柿霜糖了。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E-MAIL:dandanxi6@qq.com